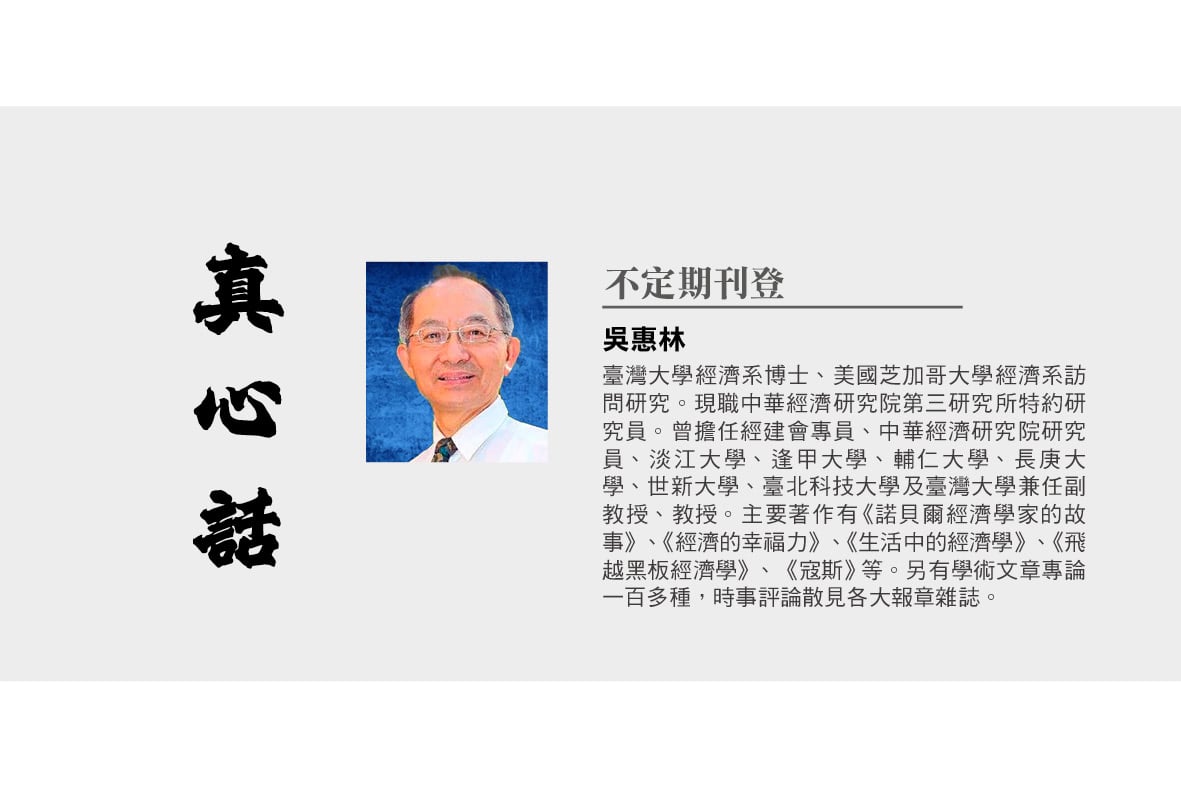1963年,史蒂格勒赴愛荷華州立學院開展其專業生涯,這是他在芝加哥大學教授們所知道的兩個可應徵的教職之一,另一個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由於瓊斯沒去任教,史蒂格勒才有機會去。如上文提過的,瓊斯是史蒂格勒的同班同學,是選擇奈特當指導教授的四位學生之一。他是一個頭腦清楚,意志堅定的經濟學家,在華府任職一段長時間,之後在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建立一個貨幣經濟學中心。史蒂格勒曾跟瓊斯說,如果當初瓊斯接下愛荷華州立學院教職,那他就可能成為西雅圖的房地產經紀商。
愛荷華學院初體驗
愛荷華州立學院支付史蒂格勒年薪三千三百美元,一個禮拜教十二小時的課,此種待遇對當時的史蒂格勒來說,是相當優渥的。不過,與五十年後相較,一周十二小時的課卻是繁重的,但對一個非學術界的人而言,簡直是太輕鬆了,史蒂格勒的岳父就說「已經得到小偷的證照了!」
史蒂格勒教授的第一堂課是「經濟學原理」,這可說是全世界的慣例,菜鳥經濟系老師擔當入門基礎課。不過這也受到很熱烈議論,因為經濟學原理很不好教,由浸淫多年經驗豐富的老資格教授擔任較合適。史蒂格勒小心翼翼地準備了十二個禮拜全部課程上半部內容的綱要,第一堂課只進行四十五分鐘,他就覺得已經講完了手中的筆記,在狼狽中撐完第一堂課,並曾擔心剩下的學期要怎麼辦?當然他很快地化解了。
史蒂格勒在愛荷華學院經濟系教課時的系主任是舒爾茲(T.W. Schultz, 1902~1998,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之一),自1934年起,舒爾茲就擔任該校經濟和社會學系主任,之後轉赴芝加哥大學任教。1946至1961年出任經濟學系主任,由於在農業經濟、教育經濟學和經濟發展的傑出先驅性研究和貢獻,於1979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艾姆斯(Ames,愛荷華學院所在地),史蒂格勒教了好幾位傑出學生,其中之一強森(D. Gale Johnson, 1916~2003),後來曾擔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和芝大副校長,而且是非常傑出的農業經濟學家,對經濟學和公共政策都有開創性和重要貢獻。他也是中共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而鼎鼎大名的林毅夫是在台灣宜蘭縣出生長大,並在台大農工系肄業,1978年獲得台灣政治大學企管所碩士,當兵期間(1979年5月16日)自金門馬山駐地游泳叛逃至中國廈門,1982年獲北大經濟系政經專業碩士,隨即赴美國芝大經濟系攻讀博士,1986年在強森教授的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次年在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隨即返回中國,1987-90年擔任中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1990-93年改任該中心農村部副部長,1994年起擔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2008年5月擔任世界銀行行政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是第一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
明尼蘇達大學教學
1938年史蒂格勒取得芝大博士學位,該年春天,在一個經濟學家會議裏,明尼蘇達大學的戈佛(F. B. Garver)教授當面邀史蒂格勒至明大任教。史蒂格勒隨即赴明尼蘇達大學擔任副教授,1945~1946學年升為教授,他在明大一直待到1946年。不過,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曾留職離開過三年,先是到「國民經濟研究中心」(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再到設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早期「作業研究」團體,叫做「統計研究群」(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參與研究服務。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友善愉悅氛圍環境裏,史蒂格勒和好朋友弗利曼(1912~2006,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共用一間研究室。他倆在芝大當研究生時就是好朋友,合用研究室後更親密、交情更深,直到1991年史蒂格勒離世,兩個人都保持友誼,兩個人都是生活呼吸和睡眠都與經濟學結為一體的人。他倆共同在明尼蘇達大學只共事一年,1946年就各奔布朗大學(史蒂格勒)和芝加哥大學(弗利曼)。
在明大這一年,兩個人合寫了一本抨擊房租管制的小書,書名是《屋頂或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這是略帶嘲諷的話語,意味著在我們頭頂上的屋頂(roofs,真實的意涵是「保護」,因屋頂可遮風避雨,也是有房住之意),或房租的上限(Ceilings, 天花板)之間,我們可以有選擇,也就是說「你要有房子住呢?還是要限樓價(租)?」頭一個字可直譯為「屋頂」,第二個字卻不是指「天花板」,而是「房租的高限」,因為美國在二戰期間要管制物價,為每一物品訂一最高價限制之,此一高價最高只能到天花板一樣的高度,不能再高了,這一限定的最高價就稱為ceiling,可直譯為「限價」。這個書名是史蒂格勒取的,顯示他一向幽默、喜愛反諷的風格。
美國從1943年開始實施物價管制,包括房租管制在內,直到1946年九月經濟教育基金會把他倆這本小冊子收入《當前問題文集》第一卷第二號出版時,房租管制仍然存在。這個書名的確受到矚目且引起熱議,基金會把該書的濃縮版提供給全國不動產協會聯合會,該會在發動反對房租管制運動時,將它印刷約五十萬冊。這本小書讓史蒂格勒和弗利曼初嚐公眾爭議的滋味。班斯(Robert Bangs)在著名的學術期刊《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寫了一篇不友善的評論,把這本文字精美、推理嚴謹、大受歡迎的小冊子稱為「政治文章」,抨擊說:「署名的經濟學家如此信口雌黃,對他們的專業絕對無益。」另有一位不友善的記者撰文說:「如果你們的學生讀完這本小冊子,仍然尊重你們的意見,我真要為他們(而非你們)覺得抱憾。」
不過,房租管制不管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或其它地方實施,都產生史蒂格勒和弗利曼預見的破壞效果。因而他們那本小冊子洛陽紙貴,一再重印再版。
關於邀請史蒂格勒到明大任教的戈佛,史蒂格勒認為是個能力頗強的經濟學家,但缺乏自信,他會自問:「如果我把自己關於這個主題的想法寫出來,我的文章會像馬夏爾(A. Marshall)的作品那樣有深度嗎?」就算史蒂格勒告訴他,以這種尺度來決定刊登與否,那麼任何領域的刊物恐怕都不存在了,也沒辦法改變他的態度。
1946年春天,史蒂格勒接到芝加哥大學「擬聘為正教授」的通知,當然非常高興。不過,聘書要在面試後,經行政核心通過才能發。史蒂格勒去了芝加哥大學,見到校長柯威爾(Ernest Cowell),因為那一天教務長哈金斯生病了。結果是:史蒂格勒被否決了!柯威爾校長說他太偏向實證了,而史蒂格勒也承認他在那一天確實是那樣。巧的是,該正教授的職位竟然給了他的好朋友弗利曼。而弗利曼在芝大經濟學系發展出舉世知名的「芝加哥學派」。史蒂格勒就說是他和柯威爾校長一起發動了芝加哥學派,因為他們兩人對弗利曼任教芝大都有貢獻。不過史蒂格勒說他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對柯威爾校長並不諒解。
據史蒂格勒兒子史蒂芬(Stephen)的分析,照理柯威爾校長不可能推翻經濟學系的要求,除非系中最有權威人物反對。當時有個由一群經濟計量學家組成的考列斯委員會(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設在芝大經濟學系,此一委員會很重視以數理方法來研究經濟學,其中有位重要人物名為馬夏克(Jacob Marshak),他是該委員會與經濟學系合聘教授,他認為史蒂格勒不夠數理化,不足以擔任教授職務。
既然芝大不聘任,史蒂格勒就轉而到布朗大學任教,該校當時是由瑞史東(Henry Wriston)極為優秀的領導之下。史蒂格勒在該校和其老友史托茲(Merton P. Stoltz)度過一年的快樂時光,之後就前往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十年。
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十年
1947年,史蒂格勒轉職到哥倫比亞大學,當時的他感到好像加入了一所真正的大學,但他覺得在哥大十年中,哥大並沒有大進步。他到校不久,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就任哥大校長。史蒂格勒指出,安排艾森豪當哥大校長,事後證明對艾森豪本人和哥大都是不明智的。因為艾森豪對學術沒興趣,對軍事較熱衷,他將時間用於研讀軍事體繫上,也為下一個事業生涯做準備,後來成為美國總統。
史蒂格勒並不認為校長和董事會是一個大規模大學改變的主因,他們是可以助長或阻礙改變,但主要的控制力量還是教授群。若教授們極想追求高水準,就能達成高水準;如果他們一點也不關心質素,就只會維持平庸水準。事實上,校長極少有「直接」權力。
史蒂格勒認為哥大是一間偉大的大學,而且擁有堅強領域的經濟學教授群。史蒂格勒到哥大,主要是由伯恩斯(Arthur F. Burns)促成的,伯恩斯後來到華府當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主席,而且當得有聲有色,之後又擔任駐西德大使。伯恩斯的能力很強,個人魅力十足,在學術上自律極嚴。據說伯恩斯在哥大接受博士口試時,被問說若身為財政部長,在面對擠提那樣可怕的財政困境、銀行資金不足,以及全面性的財政災難時,該怎麼辦?伯恩斯回答說,他將會從哥大敦請一位年輕、聰明、紅頭髮的經濟學家(指的是提問的教授)來處理這些問題。這個回答雖惹毛了那位教授,但其他在場的口試委員卻覺得非常有趣。伯恩斯擔任聯準會主席時表現優異,史蒂格勒的一位朋友就說,伯恩斯的表現就像是把一隻手綁在身後,卻仍能贏過華府的任何經濟學家,史蒂格勒也很認同他朋友的評價。伯恩斯的口才非常好,對於很多人和很多課題都有新創觀點。他講話時故意豪放,跟寫作時句斟字酌完全不同。據說很多國民經濟研究中心(NBER)的職員,都曾因順道去和伯恩斯聊了一下,因而錯過吃晚餐。
在哥大,史蒂格勒還有一些傑出的同事。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維克瑞(William Vickey, 1914~1996)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政府租稅和公用事業定價兩個層面,有豐富的開創性觀念及應用,使人類對保險與信用市場、賦稅制度、競爭條件,甚至公司內部組織等等的全面經濟活動,都有較佳的理解,他在拍賣理論上也有卓越成就。除了維克瑞外,當時史蒂格勒的哥大同事還有專長國際貿易的納克史(Ragnar Nurkse)、公共行政方面的夏普(Carl Shoup)、公共事業方面的波布萊特(James Bonbright)、經濟統計方面的密耳斯(Frederick Mills)、經濟史方面的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以及經濟思想史方面的竇夫曼(Joseph Dorfman)。史蒂格勒自己教授的是經濟理論、歐洲的經濟思想史,以及產業組織。
回歸芝加哥大學
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到1958年,史蒂格勒就回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服務,可說是回到他所歸屬的學園,因為在智識上,他無疑地長久以來就是它的一員。上文已提過,在1946年春天,史蒂格勒就有機會回芝大任教,但陰錯陽差下被弗利曼取代了,這對史蒂格勒造成深重的打擊。由之後他數度拒絕芝大延攬的事實可充份得知,史蒂格勒不是針對弗利曼,而是對芝大當局不諒解。
1958年史蒂格勒為何會答允回歸芝大呢?因為那是他的好友瓦列斯當芝大商學院長所提出的邀請,而且該職位相當優渥。那就是渥爾葛林(Charles R. Walgreen)講座教授,該職位的起源是這樣的:1936年老渥爾葛林先生為其在芝大就學的姪女辦休學,並且控告芝大教自由戀愛和共產主義之類的理論。這項消息被《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炒熱,伊利諾州的州議會就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結果證明芝大清白,渥爾葛林先生為了表示歉意並相信芝大無辜,乃贈送五十萬美元給芝大設立特別講座。二十年後,史蒂格勒就是頭一個獲得該獎座殊榮者,年薪兩萬五千美元,在當時經濟學界是非常耀人的數字。史蒂格勒同時兼教經濟學系與商學院,他非常滿意這樣的安排,因為經濟學系和商學院的教授都擁有不平凡的特質與知識。
史蒂格勒回歸芝大之後,終其一生未再他就,和其他傑出同僚奠定「芝加哥學派」的鼎盛時代。他認為芝大是最好的大學,雖然到1992年時就一百年了,卻奇蹟似地持續年輕和熱情。就是因為還有追求知識的浪漫承諾,才不太顯現稚氣,也或許因為如此,才會經常有重大的新知識出現。芝大的友愛氣氛頗為濃厚,即使同事們的工作不太相關,仍然會分享彼此的問題,大家都仔細閱讀論文初稿,且提出建設性批評,而作者也會同等回饋。有一位有名的經濟學家告訴史蒂格勒說:「離開芝大以前,我從不知道教授也會寂寞。」而史蒂格勒表示感同身受,他認為芝大這種允諾研究的延續力是少有的,更可敬的是,芝大許許多多的教授群長期都如此,而且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這種風氣會自我強化。被這種學術氣氛和程度吸引的學者,就是那些會加入芝大教授陣容的人。當史蒂格勒從哥大回到芝大時,芝大並不以年資替代研究成果,對史蒂格勒是有利的。
對於像芝大這樣人文薈萃的地方,史蒂格勒覺得是不常見,甚至是反常的。他指出,倫敦經濟學院掌控了1930年代的潮流,而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系,在薩繆爾遜時代也在研究上有過同樣的情況。史蒂格勒認為,好的溝通在偉大的大學是必須的,他相信極佳的溝通體系是芝大在1960年代後期,在其他多數大學頻傳暴動時,仍能維持校園安寧的主因。因為教授們團結支持學校開除頗多的野蠻年輕人,這些年輕人準備用暴力壓抑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的傳統價值,以達成他們強硬的要求。不過,史蒂格勒認為這些年輕人的罪惡比許多學者來的輕,那些學者一面批評高壓手段,一面卻公開同情學生把大學政治化的慾望。如果沒有這些學者廣泛的同情,學生運動將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而且不會在校園裏留下政黨意識。(待續)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