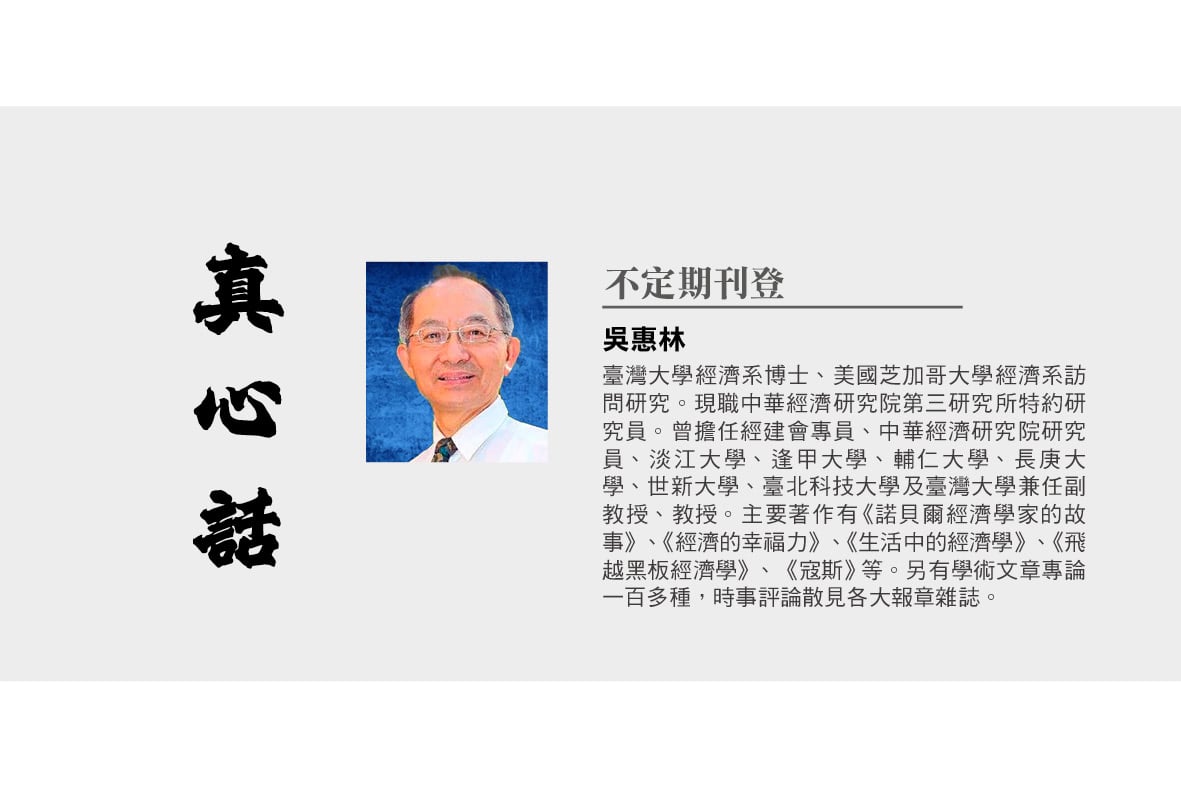「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顧名思義,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Ronald Coase,1910—2013年)的理論,如今已名聞遐邇、大家琅琅上口,即使其真意或許不那麼地被真懂,而且其出現也經過一番的波折,有意思的是這個名稱還是史蒂格勒命名的呢!
萬歲!我找到了!
史蒂格勒指出,科學的發現常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試驗探索才產生的,在其背後總有許多漫長卻走不通的死胡同。半熟的概念形成假說,而更生澀的概念要克服馬上會遭遇到的困難和矛盾。像阿基米德(Archimedes)那樣,突然想到一個偉大的概念就大叫「萬歲!我找到了!」是難得一見的英雄。史蒂格勒的專業生涯都是在一流學者的群體中度過,但只有一次經歷到類似阿基米德那樣突發的狂喜表態,而且他還只是個旁觀者呢!
話說1885年到1924年,在英語系世界裏,最有名的經濟學家是馬夏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他是英國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馬夏爾是一位具有豐沛想像力和奇思怪想的人,開創了很多課題,包括「外部性經濟」——這個東西會影響一個企業,卻不會受任何一個企業的明顯影響。例如:假設在一個區域有三十個煤礦,假如它要進行開採的話,就要用幫浦把水從較低的豎坑中弄出來。若這片土地有很多相通的孔,若其它的礦坑以幫浦排出越多的水,自己的礦坑就可以少抽些水,可是,沒有「一個」煤礦以幫浦排水的行動會顯著影響水位。因此,越多煤礦坑進行開採,每個礦坑抽出的水越多,任何一個煤礦抽水的成本就越低。
馬夏爾是「新古典經濟學」開創者,被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他在劍橋大學的「教授」頭銜是由庇古(A.C. Pigou,1877—1959年)承繼而來。庇古在他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Welfare)這本名書裏,花了大量篇幅討論「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由於沒有一個煤礦的抽水會對這地區的水位產生明顯的影響,因此,每個礦坑的所有主在決定要抽出多少水時,會忽略它的抽水行為對其它煤礦的好處,因為他沒有分享這些好處。所以,從整個產業來看,抽水會抽得太少。庇古於是建議,這類的「外部經濟」可由政府補貼,譬如給每個煤礦主10%的抽水成本。
相反地,「外部不經濟」通常是以一個排放黑煙的工廠來說明,該工廠所排放的黑煙會使鄰近的一千戶人家每戶每年多花費十美元的洗衣費。庇古乃建議政府對這家工廠課稅,或更正確地說,對該黑煙課稅。最理想的結果或許可以減輕一半的黑煙排放,從而帶給鄰近住戶五千美元的利益,但只增加該工廠三千美元的花費去減少一半的黑煙排放。
這種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所謂的「外部性」(externality),其導致私人和社會利益的不協調,早已經成為經濟學界的真理。經濟學家接受這個真理的方式,就像他們接受供需決定價格的主因一樣,本能而且毫不懷疑地接受。所以,當1960年寇斯在一篇精妙地分析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的管制不當的論文裏(這篇論文被產權名家張五常教授極度稱讚為「論文範本」),相當不經意地批評庇古的理論時,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們實在很難理解,為甚麼像寇斯這樣傑出的經濟學家,竟然會犯如此明顯的錯誤。由於該文投稿到芝大的《法律與經濟學期刊》(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主編達瑞克特(Aaron Director)雖認為該文傑出,但對寇斯的論點存疑,於是詢問多位芝大經濟學教授,大家都有同感。達瑞克特將所有的反對觀點都轉達給寇斯,但寇斯堅持己見不認錯,堅持不改,這樣的書信往返很多次,最後寇斯回信說:「就算是我錯好了,你也不能否定我錯得很有趣味,那你應照登吧!」達瑞克特回信說:「我照登是可以,但你必須答應在發表之後,到芝加哥大學來做一次演講,給那些反對者一個機會,親自表達他們的反對觀點。」寇斯回說:「演講是不必了,但假如你能選出幾位朋友,大家坐下來談,我很樂意赴會。」達瑞克特乃順從寇斯,邀請近二十位來自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和寇斯,在某個晚上會集在達瑞克特家裏,由他請客吃晚餐。飯後大家坐下來,由寇斯先發言,他要求大家暫時假設,世界上沒有交易成本。史蒂格勒認為這要求是合理的,因為經濟理論家跟所有理論家一樣,都習慣於(其實是被迫的)處理簡化的,因此常是不實際的「模型」和問題。不過,史蒂格勒說,零交易成本仍是一個大膽的理論架構。比如說,零交易成本意含,購買汽車時,每個人都知道所有經銷商的售價(對任何人而言,沒有時間或金錢的成本),那麼,每個人都可以非常確定所有保證包換有缺陷零件,或提供服務的真正內涵,而且也對保證的執行具有充份的信心(沒有爭議)等等。零交易成本意謂這個經濟世界沒有衝突或曖昧。
接著寇斯要求與會者推論,在這樣的抽像世界哩,將沒有外部經濟或外部不經濟的現象。史蒂格勒猜測,他們沒有太多爭論就接受了這個推論。上述例子的三十位煤礦主可擬訂一份契約,註明每個人應抽多少水(或予適當補償),使該行業的利潤最大。既然明訂契約的會議和執行這個契約沒有成本,這個結果自然是可能的。事實上,就算有三千個煤礦主,這種會議還是免費的。在零交易成本的國家中,律師將會消失。
不過,寇斯要求與會者也相信,在零交易成本裏的第二個命題:不論誰承擔法律上賠償損壞的責任,或不論誰擁有法律上的所有權,都不會影響經濟資源的使用方式!史蒂格勒他們強力反對這種異端說法。史蒂格勒說,跟平常一樣,弗利曼說了最多話,也思考了最多。該場歷時兩小時的爭辯,從原先二十位反對,一位贊同寇斯的觀點,竟然轉變為二十一位贊成寇斯觀點,沒人反對的局面。史蒂格勒感性地說:「這真是令人愉悅的交談!」也在事後對於他們沒有敏銳的洞察力把它錄音下來,大嘆可惜。
該場辯論由寇斯舉出的一個栩栩如生例子開始:一個牧場主人與穀物農夫為鄰,有時牧場的牛會侵入毗鄰的農地,因而破壞農人的穀物。究竟是牧場的主人要賠償農人的穀物損失,或是穀物的主人要自負損失,這對牧場的養牛數量和穀物的產量,是否會有差別呢?寇斯的回答是:「不會」!
有一種方法可以使寇斯的答案似乎有道理,那就是讓穀物農地和牛隻牧場都是一個人擁有,再問所有主會怎麼辦。這位單一的所有者應會結合兩種事業,俾達到最高利潤。譬如,若增一頭牛會使養牛的利潤增一百美元,但會降低穀物利潤一百二十美元,他就不會增養那一隻牛。同樣地,若圍起一個籬笆,在其使用年限裏,能節省穀物損失的價值抵得上圍籬笆的成本,他就會建一個圍籬。如果牧場和農場分屬兩人,他們也可以利用契約達到那種最適狀況,而他們之所以會同意這樣做,就是因為這樣會讓他倆可以瓜分一個更大的利潤餅。推定誰承擔穀物損害賠償的法律責任,只是決定誰要給付給誰的分配問題,並不會影響農地的穀物種植和牧場的牛隻飼養之最適方式。
「寇斯定理」出爐
史蒂格勒希望這一個命題經解釋一次後,就會顯得合哩,甚至會變得極其浮顯。該命題是:當沒有交易成本時,法律上產權的指定對經濟企業中資源的分配沒有影響。對於這個命題,專業的經濟期刊還是刊登了相當數量的「反駁」論文。史蒂格勒宣稱,是他將這個命題命名為「寇斯定理」的,迄今已膾炙人口、廣為人知。由於科學的理論很少依據第一個發現者命名,所以,這是正確的歸屬貢獻者給首創者的罕見例子。
回到現實世界來,交易成本是「不可能」為「零」的,即使是簡單的交易,如美元兌換德國馬克,也要交易值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成本。若你將一美元兌換為馬克,再將馬克兌換為美元,你若能剩下九角六分就算幸運了。若你將一千美元兌換為馬克,再兌換回美元,就會剩下九百六十美元多,因為愈大筆的交易,手續費相對低。兌換現金是需要成本的,觀光客必須支付。不過,寇斯定理是饒有趣味的,因為交易成本的大小限制了外部經濟或外部不經濟的程度。
如果你不是經濟學家,很可能會說,寇斯這個論點是蠻漂亮,但有甚麼令人興奮的呢?一個沒有交易成本的世界,其實是很難達到的環境,或者說是現實人間根本沒有的,哪裏還會有許多奇怪的現象呢?史蒂格勒要大家想想看,一個社會如果質量定律不再運作,而且每咬一口就縮小體積,那將可能產生哪些古怪的事情!
史蒂格勒說他必須公正地說,懷疑寇斯定理有甚麼值得興奮的,是有幾分道理在的。他說:「理論家喜愛新而奇怪的架構,用以創建一個新的世界或改變看待當前世界的方法。」在1980年代末,學人們已開始研究「交易成本」的本質和大小,那是過去應做而沒做的。不過,在寇斯定理公開後大約三十年間,這方面的研究還是出奇地少。史蒂格勒認為,值得為寇斯定理興奮的理由有一些不同:這個精巧作品立即改變人們看待和研究許多層面的經濟問題的方式。史蒂格勒舉了一個例子。
他指出,職業棒球的「保留」條款長期以來讓球隊控制職棒球員自由轉隊的權利(該條款在當時已刪除了)。該條款意謂著,如果某個球隊成功地首先和某個未來明星簽約,該球隊就可以說該球隊能夠永遠留住他——即使他轉去別隊可能會更有價值(就門票收入而言)。寇斯定理告訴我們,這種說法是錯的,球員還是會被賣到他最值錢的球隊去。因為契約的協商並不是太難的事,而新舊球隊和這個球員都會因該球員轉隊而獲利。保留條款只是影響到該球員能分到多少他對門票收入的貢獻,保留條款並不會讓他待在錯誤的球隊裏。
寇斯定理的例子不勝枚舉,但棒球員的契約這個例子,史蒂格勒認為應該可以說明它使人興奮的本源。寇斯定理出現以後,人們看待很多問題的方式是改變了。人們希望知道,經由協商是否可以找到雙方都能獲益的解決方案。而寇斯定理這種看待問題的方法,史蒂格勒認為,已經引起廣大的效果。他說,想想法律訴訟解決爭論的做法:為甚麼對契約有爭議的雙方不進行妥協,從而節省雙方必須為訴訟所作的花費?而事實上,一般而言,爭議雙方通常會互相妥協,只有一小部份的爭執會對簿公堂。大部份的法院訴訟案件,都緣於雙方預估勝訴的可能性時,存在很大差異所致。當事實和法律條文都很清楚時,訴訟案應該會在審判前解決。因此我們並不訝異看到,寇斯定理滲入卓越的法律學院,並在課堂和法律期刊上引起莫大的注意,且被廣泛運用到民事、財產和契約等方面。寇斯後來成為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正是他這個天才的適當歸宿。
史蒂格勒認為,開創性通常是要用新的方法來看待熟悉的事情或想法,他對經濟理論的最重要貢獻,自己認為或許是把資訊當成是有價值的商品,可以生產、也可以購買。史蒂格勒之所以對資訊問題的研究感興趣,是起源於他注意到——就好像歷史上每個購買者都會注意到——一個人可以貨比多家,從而買到較便宜的東西。但是,經濟理論裏的標準定理,是假設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在一個市場裏只有一種同質的財貨和一種價格。這個定理只是簡單地指稱,買賣雙方都會探詢價格,且排除價格上的差異。例如,只要有一個賣者願意接受比買者想付的更低價格時,這位買者就會找他買。為了讓這個定理得以適用於可觀察到的價格差異——即使是同質的產品(比如三十家五金店對某個特定工具的售價)也有價格差異,史蒂格勒探索人們完成搜尋更好的價格之障礙,終於在資訊成本中找到答案。要發現每一位賣者的售價和他所提供其它服務的品質,如充份的存貨和退換瑕疵品的迅速成度,必須花費時間和交通成本。這項結果可以說是寇斯的研究成果之補充說明,因為史蒂格勒考慮了交易成本的主要成份,且事實上,他的文章跟寇斯的文章大約是同時出現。
資訊理論的開創
資訊這個角色,在經濟理論裏早已快速擴大。曾經有一年出現了十二篇以上的文章,討論當一方(如賣方)比另一方(買方)擁有更多的產品品質資訊時,會產生哪些問題。艾克羅夫(George Akerlof,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檸檬」‧(lemons,意即次級品)理論。該理論是說,假設只有二手貨汽車的賣方才知道車子的品質,潛在的買主將會正確地假設劣等品質汽車所有者,才會特別想要賣掉他們的車,所以這些潛在買家只會願意支付最劣質汽車的價值之價格——這樣一來,只有最劣質的舊車才會賣到二手貨市場。(這種不好的循環是可以打破的,如賣者設法取得值得信賴的品質保證。)
曾是史蒂格勒學生的奈爾遜(Phillip Nelson),把資訊理論作了基礎性的延伸,運用到廣告行為上。他證明所謂的「金字招牌」廣告招式(「我們公司是這行業裏最老牌或最大者」)就是要對顧客提供值得信賴的保證:這個公司一定對待顧客非常好,不然他就不會有這麼多老顧客了。而經濟學界在討論促銷廣告上,已經比過去數十年細膩許多了。
由於科學的發現通常起源於,以不同的觀點看待熟悉的現象,所以,很多科學理論會由幾個人各自不相干地發現。時常發生的情形是,先驅的研究領域碰到障礙,而該領域的數位學者可能都會找到解答。的確,即使是這些多重發現者,也可能只是再次發現者而已。譬如說,1871年時,傑逢斯(W.S.Jevons,1835—1882年)和孟格(Carl Menger,1840—1921年),以及三年後的華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年)都指出,消費者行為可從每個人會努力運用他的資源購買財貨以獲取最大的滿足(邊際效用理論),來加以了解。這個觀點導入經濟學後,產生了所謂的「邊際革命」。史蒂格勒說,有一位可憐地遭忽略的德國小公務員哥森(Heinrich Gossen),早在他們十七年前,就已經用較好的方式提出了這個理論,而且還有其他更早的前輩呢!
創見者的爭執
在此情況下,誰是最先提出者,自然會引起爭執。社會科學的偉大人物摩騰(Robert K. Merton,1910—2003年),曾經就提出科學發現的先後次序對學者的重要性,做過一次扣人心弦的演講。他指出,為了爭取被肯定為最先提出某個概念的地位,平常鎮定而寬大的學者,都會變成粗魯的鬥士。他舉出很多例子,如牛頓(Isaac Newton,1642—1726年)和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之間曾爭執誰是第一位發現微分學中的差分內容。
到1980年代末,諸如此類的爭執不再激烈或冗長,事實上,在20世紀或可能也包括19世紀的經濟學界裏,沒有真正有趣的爭執誰優先發現的重大事件。不過,確實常有人宣稱他是遭受忽略的發現者,但並沒有徹底的挑戰,遑論有重大剽竊的指控。根據史蒂格勒的印象,在其它的科學領域,爭論誰是最早的發現者之現象也同樣退燒。造成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專業性期刊已是學者間溝通的唯一重要管道,而提出概念的日期比較容易判斷了。
史蒂格勒認為,任何當代的概念或理論,要說是沒有先驅者曾提出其中的一部份,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歷史上充滿了聰明、富創造力、好奇的心靈,意欲解答大部份的實際問題和很多想像的問題。一個當代學者只是一群有能力、同心致力於特定領域或主題研究者之一,並且把一點點的新知識(包含理論和實證兩方面)頻繁地加入知識的共同池塘。這個既存的知識池塘就是下一個新發現不可或缺的基礎。這不隱含新發現必然會產生;每一個科學領域都曾經有過或停滯,或緩慢,而且進展平淡的時期。
學者間的相互依賴以及他們共同依賴於已經完成的研究之現象,早已有日趨強烈的趨勢。就經濟學來看,英國的研究重心在十九世紀後半移到大學裏(英國是當時的世界領導者),美國和西歐的情形,在時間上也差不多。經濟學家的數量,在馬爾沙士對人口成長做了可怕的預測後暴增。美國授予經濟學博士的人數,在1900年只有將近十人,而1980年時,已達677人。
隨著經濟學家數目的增加,經濟學術期刊也開始出現:1886年哈佛大學發行《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892年芝加哥大學發行《政治經濟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890年英國王家經濟學會(Royal Economic Society)發行《經濟期刊》(Economic Journal)。到1980年代,英語系經濟期刊的數量有150—200種。由於研究的交流急速增加,對一個主要大學的經濟學家來說,不知道重要的發現,或完全了解許多的新發現,是很有困難的。
科學家數量的成長和交流方面的長足進步,使得人們懷疑,個別的學者恐怕很難做到英雄式的往前躍進的新發現。物理和化學諾貝爾獎早就越來越多次頒發給兩個或三個得獎人,就是那些得獎人個別的貢獻還不夠深遠之明證。而經濟學這門較年輕的學科,自1969年開始頒發諾貝爾獎,就是兩位學者同時獲獎。1901到1920年間,物理和化學諾貝爾獎有31次頒給單一得獎人,3次頒給兩位得獎者,只有一次是頒給3個得獎人(得獎人數的最高限)。從1961年到1980年,有18次頒給單一得獎人,12次頒給兩個得獎人,11次頒給三個得獎人——平均而言,每次大約頒給兩個得獎人。至於最晚成為諾貝爾獎學門的經濟學獎,在1969到1978年十年間,五次頒給單一得獎者,也有五次頒給兩位得獎者;在1978到1988年十年中,有九次頒給單一得獎者,只有一次頒給兩位得獎者;在1989到1998十年間,有五次頒給單一得獎者,三次頒給兩位得獎者;有兩次頒給三位得獎者;在1999到2008年十年中,三次頒給單一得獎人,五次頒給兩位得獎人,兩次頒給三位得獎者;在2009到2018年十年中,有三次頒給單一得獎者,五次頒給兩位得獎者,兩次頒給三位得獎人;至於2019到2024年最近六年中,各有一次頒給單一得獎者和兩位得獎者,其餘四次都頒給三位得獎人。似乎單一位得獎者越來越少了。
史蒂格勒設想:人們可能會問每一位諾貝爾獎得獎人,如果沒有其他未得獎者的研究成果,你有沒有可能達到這些成就?他想誠實的答案大部份是很快地回答「不可能!」史蒂格勒進一步指出,探討科學裏主要或甚至次要概念的源起,不可避免地會使科學研究的本質傳奇化,它會成為英雄式進步的小故事,或是勇敢而成本高昂的努力。儘管如此,重要的個人進展以及大膽的冒險都只是科學工作的一小部份,就好比冰山一角的表皮。科學研究是一個市場過程,跟雜貨店老闆或電腦製造商的活動相較,只是形式大不相同而已,本質上鮮少差異。個別的學者,藉著自利行為推銷自己。如果總體經濟學或電腦科學開始蓬勃發展,那剛畢業的學生進入這些領域的人數就會開始增加。
史蒂格勒指出,學者的酬勞通常不是依其研究件數來按件計酬,但實際上還是相關的,研究成果愈好,就愈能在較有威望的期刊發表。傑出的研究者會被較好的大學聘用、升等也較快速,也比較容易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和私人基金會的補助,而且教學的負擔也會較輕。在物理學界,還會較容易主持人手齊全的實驗室。而學者的組織(如各式各樣的學會)也會選舉較傑出的學者,以及較具技巧的學界政客,作為領導幹部。
誰能決定要研究甚麼主題,以及誰能判定每項研究成果的優良程度?短期間(一年以內)是由同儕科學家來判斷。如果這個主題有點複雜,立法委員、官吏和大學的行政管理者就很難了解這個正在進行的研究,也就更無法指導其研究方向了。科學的掌舵者乃是該領域中卓越的專業人才,他們擁有使自己不朽和自我選擇研究方向的特質。
史蒂格勒認為,藉由自我選擇精英來組成科學的管理體系,可能會產生類似18世紀牛津和劍橋大學那種顯得愚蠢的停滯且墨守傳統教條的結果,而這些弊病卻沒在美國出現。美國擁有很多好大學、很多基金會、很多科學期刊,使得每一科學領域都成為完全競爭的行業。沒有一個正統的模型可以主導一門科學,但在聯邦政府贊助研究扮演有力角色後,集中管理的趨勢可能性已經升高。
競爭性環境較佳
邊大衛(Joseph Ben-David)這位著名的社會科學家認為,美國的某些科學領域之所以能取得世界領導地位,主因是美國的科學界比法國或德國較不集中控制之故。競爭性的科學環境相較嚴密組織的科學體系,對新的概念較為開放。既存的體系反對完全創新的概念,並不只因為它們經常是錯的這個好理由,還因為一旦新的概念是對的,目前掌控體系的領導者的知識,就會變得過時或毫無價值。
史蒂格勒認為,競爭的過程會產生實質的共識,當他在史丹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Behavioral Sciences)工作那年(1957—1958年),同僚經濟學家有亞羅(Kenneth Arrow,1921—2017年,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弗利曼、瑞德(Melvin Reder,1919—2016年)和梭羅(Robert Solow,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群人的最大共通處是能力高超。有一次,中心主任泰勒(Ralph Tyler,1902—1994年)拿出一長串未來可能會聘入中心的名單,要他們從「絕對贊成」到「絕對不贊成」四個層次表達意見。由於他們幾個人的看法極為接近,泰勒指責他們相互勾結,其實他們並沒有。
史蒂格勒表示,從長遠角度來看,科學的組成和問題並不能自我不朽,遲早掌握權力者一定會要求成果或更好的成果。而這些成果並不需要只是實用的(如治療某種疾病或某種不景氣),但他們得滿足社會的一項重大要求,那就是研究成果必須值得其所花的費用。史蒂格勒覺得,即使在這方面,競爭的特質也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比如以不同的科學領域間的競爭來解決重要的課題——物理和化學的結合就是顯例,而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科學界也以競爭來決定領導地位。德國和法國的經濟學界,數代以來都受控於非理論的傳統(德國是歷史的分析,法國則是社會學的分析),兩個國家都臣服於較成功的英、美的經濟學。
遭妒的美國經濟學界
在美國,20世紀的經濟學家在推銷他們的成果上,成效卓著。每一家大企業至少僱用一位經濟學家,政府這家最大的企業則設有經濟顧問委員會,而在適當的時機下,該委員會得以進駐白宮。自從諾貝爾獎設立後,唯一增設的獎項是經濟學獎。而經濟學通常是大專院校裏最受歡迎的科系:要麼進法律學院,要麼進商學院。所有那些關於經濟學家之間意見差異的乏味幽默(五個經濟學家會有六種意見,其中兩種意見是凱因斯提出的),或是他們沉迷於抽像的思考(「實際上是可行的,但是理論上行不通」)。史蒂格勒認為,這些事實上都是嫉妒的嘲弄,而公然責難美國則是統合歐洲知識份子的唯一法寶,批評經濟學是聯合其它社會科學對抗美國的主要武器。畢竟嫉妒比起同情,是會多出幾許甜言蜜語的。
1982年,史蒂格勒由於對資訊經濟理論和公共管制理論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說自己在得獎前,並沒有聽到任何傳聞,只是聽到其他經濟學家將會獲獎的傳聞,所以得知自己獲獎的消息,讓他有若奇蹟式的驚訝。
史蒂格勒回憶,在斯德哥爾摩的慶祝會是很棒的盛會。他的三個兒子和他們的太太及四個孫子,他的老朋友比恩(Water Bean),以及弗瑞德蘭(Claire Friedland)陪他一起參加頒獎典禮。他覺得人們一定會對瑞典王室致以最高的尊敬,特別是王室成員包括一位嫵媚迷人的王后。
不過,史蒂格勒卻對該種獎的目的和它為得獎人博得巨大尊崇的理由感到困惑,特別是他在閱讀過札克曼(Harriet Zuckerman)在1997年對諾貝爾獎有趣的研究——《科學精英》(Scientific Elites)——這一篇文章之後。諾貝爾(Alfred Nobel)當初是希望這些慷慨的獎金,可以提供給得獎者充份的經濟獨立,以便他們能奉獻餘生於研究上。可是,即使是1901年時的原始獎金(4萬2千美元),也不能提供經濟獨立所需,而1980年代末的獎金(通常由兩個或三個得獎者平分,且自1987年起還需繳稅)最多只相當於一位傑出教授一年薪水的三或四倍。當然,得獎人也會因為獲獎而有別項收入,在經濟學界,演講費和演獎的邀請會倍增,但這種收入必須去賺取才能獲得。
諾貝爾獎的目的,並不是要引起該科學領域的同儕去注意得獎者的重要研究成果。畢竟平均而言,得獎者獲獎的研究成果要發表大約十三年之後,才會得獎。在這十三年間,有能力的科學同儕就已知道得獎人的研究,並應用這些成果了,只有不夠能力的人,才會認為得獎對研究目的具有新聞價值。
史蒂格勒認為,諾貝爾獎倒是對具有獲獎資格的科學領域,提供了吸引人才的額外誘因。他說,如果亞當‧史密斯的信念是對的,亦即,人們會高估他們贏得任何彩券巨額獎金的機率,那麼,諾貝爾獎就可能已稍微鼓勵了有能力的年輕學者進入可獲獎的領域裏,且稍微壓低了這些領域的平均收入。史蒂格勒認為,這種聰明才智的重分配,是否對社會有好處,還很難說,因為我們沒理由相信,可獲獎的領域會吸引到才能較差的人,而不能獲獎的領域會吸引到才能較佳的人,蓋一切仍依個人預期的邊際產值而定。
諾貝爾獎的迷思
史蒂格勒認為,諾貝爾獎的主要效果,就是讓得獎人在非科學家裏獲得崇高聲望,而在這方面,該獎已顯著成功。每年的頒獎典禮受到媒體的廣大注意,這一定讓每個促銷人員嫉妒。對受過中等教育的公民來說,他們不可能了解得獎人的研究成果,也難以找到那些成果和當代幸福的關聯性。即使是沒受過教育的人都會知道,獲得這個榮譽標誌的人是科學中的男爵。
不過,如此的榮譽提供了甚麼社會服務?而該聲譽招惹了一些損害則頗明顯:一大堆由得獎人署名的公開聲明集結出版,而那些聲明的內容根本不是得獎人熟悉的專業,且這種出版品是令人沮喪的。然而,公眾尊崇的聲譽之好處何在呢?
史蒂格勒認為這是一個問題,而不是遮掩式的抱怨。公眾對他們所做的事都有好理由,而發現這些好理由則是社會科學家的工作;儘管很多人會覺得,去取笑公眾的行為比發現行為背後的理由更有意思。史蒂格勒是這樣推測的:公眾想要崇拜在適當行業裏的傑出表現,例如運動、軍事以及科學層面等。如果有衡量科學表現的客觀標準,例如次原子(質子和電子)的發現數量,公眾就會以這個基礎來選舉冠軍,而不會去依靠可能犯錯的瑞典學院和其它學術機構。可是,這是他們目前擁有的最好準繩,因而他們把榮耀堆積在得獎者身上。
史蒂格勒問說:為甚麼公眾要對各領域的傑出表現給予喝采?難道他們擁有一個崇拜基金,必需把它用掉?他的推測是:這種喝采是希望刺激各領域真正重要的成就。而重大的科學成就經常是高風險工作的成果。這種引出學術圈中的重大成就之誘因結構,總是依賴於聲望和研究設備。即使是在前五十名優秀大學裏的最高薪教授,他的薪水也很少是最低薪教授的三倍。既然瑞典學院願意集中焦點於少數幾個人的傑出成就之聲望,自然有助於矯正大學和當前社會平等主義結構之弊病,從而得以提供誘因去進行高風險的研究。
這樣看來,諾貝爾獎得獎人數未能與可獲獎的科學領域數目維持相稱的增速(得獎人數太多),並非重大缺失。而重大缺失之一是它排除了一些知識上的競爭激烈、且歷史上曾大放光彩的科學領域之獲獎資格。因此,至少到1980年代末,史蒂格勒指出,像拉帕勒斯(P.S. Laplace)那樣偉大的人,都沒資格得諾貝爾獎,因為天文力學尚非該獎涵蓋的科學領域。史蒂格勒自忖:不知道許多其它的獎項(如數學界的Field獎)是否足以滿足這種需求?#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