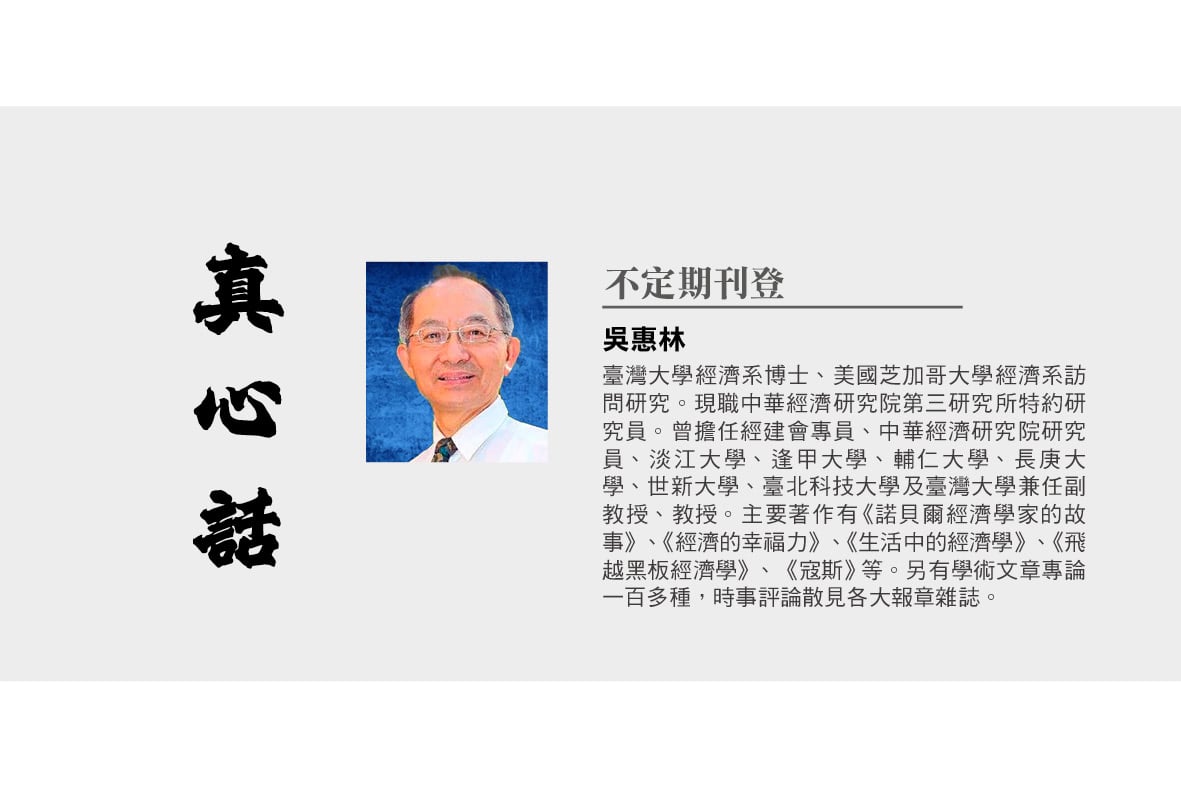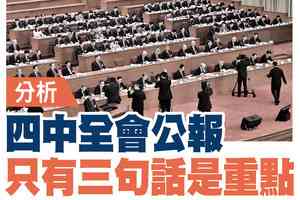史蒂格勒是當代傑出經濟學家,不但長於理論,更擅長以實證得出證據作為論證的有力基礎。他不但開創了經濟學的新領域,對學術界做了重大貢獻,也因為具有幽默、機智,以及優美的文筆,將枯燥的學理通俗化的傳達給大眾,對社會各階層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胡佛研究所主任坎貝爾就曾開玩笑的說,如果每位經濟學家都具有史蒂格勒的表達方式,經濟學也就不至於被冠上「憂鬱科學」的稱號了。據說史蒂格勒將其小船命名為「論文」(treatise),如此一來,有人問他空閒時所為何事時,他即答曰:「從事論文的工作。」
在當時的芝加哥學派者中,弗利曼、史蒂格勒和瓦列斯三人,被稱為「三劍客」,這三人中,以弗利曼的名氣最為響亮。其實,不論文采、演說口才,以及學術理論,或通俗作品等方面,史蒂格勒都不遜於弗利曼,而在公共政策的影響力這個重要課題上,史蒂格勒的貢獻也許還更有過之呢!
史蒂格勒的研究領域主要有三:一般經濟理論、思想史,以及產業經濟學。其學術著作也集中在這三方面,他自己在《經濟學名人錄》中列舉十本書和七篇論文當代表作。十本書分別是《生產和分配理論》(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1941)、《價格理論》(The Theory of Price,1942)、《五大經濟問題講詞》(Five Lectures on Economic Problems,1949)、《科技人員的供給與需求》(Supply and Demand for Scientific Personal,1957)、《經濟學佈道家》(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 and other Essays,1963)、《製造業的資本和報酬率》(Capital and Rates of Retur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1963)、《經濟史文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1965)、產業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1968)、《產業的價格行為》(The Behavior of Industrial Prices,1970),以及《人民與國家》(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Essays on Regulation,1975)。
七篇論文分別是〈短期的生產與分配〉(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Short Run,發表於1939年6月份的《政治經濟期刊》(JPE))、〈生存的成本〉(The Cost of Subsistence,發表於1945年5月份的JPE)、〈拗折寡佔需求曲線和僵固價格〉(The Kinky Oligopoly Demand Curve and Rigid Prices,刊於1947年10月份的 JPE)、〈分工受限於市場的擴張〉(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刊於1951年6月份的JPE)、〈資訊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刊於1961年6月份的JPE)、〈寡佔理論〉(A Theory of Oligopoly,刊於1964年6月份的JPE)、〈法律的實施、執法者的不法行為和補償〉(Law Enforcement,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刊於1974年1月份的《法律和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史蒂格勒在學術上的主要貢獻幾乎都呈現在這些篇章裏,依史蒂格勒自己的歸納,分成七大貢獻領域:
一、資訊經濟學
那篇1961年同名的文章是開創性的著作,文中指出,資訊的蒐尋是有成本的,而且當蒐尋的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效益時,才會停止蒐尋。此時所獲的資訊,就是最佳資訊數量,而且資訊價格也同時決定了。此種資訊經濟學的發展,不論在學術研究或實際問題的應用都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二、管制經濟理論
這部份的精彩論文大都蒐羅在《人民與國家》這本書中。史蒂格勒將管制當成一種「特殊商品」,也經由供需雙方互動來決定管制數量,同時也經由供需來推論管制的「獲益」對象。這個領域的影響既深且遠,例如後繼者佩爾斯曼(S.Peltzman)更是做了許多的「實證研究」,將管制的起源和性質都作充份研究。他的膾炙人口的著作當屬對「醫藥」和「安全帽」管制的實證,統計實證的結果,發現管制的弊大於利。自1940年代以來,經濟管制逐漸蔚為主流,連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在2020年代予以肯定。為了興利防弊,史蒂格勒的經濟管制之著作更特別值得各界閱讀和省思。
三、食物問題的直線規劃
這就是上文所引的〈生存的成本〉那篇文章內容。
四、寡佔勾結理論及其限制
上提的第六篇文章就是探討此課題,這是繼二百多年前亞當‧史密斯的一番說詞:「同業者即使為了消遣,也很少聚在一起,而他們的交談,往往以一項不利於公民的陰謀,或某項漲價的計策為目的。」史蒂格勒針對這種現象,研究得出在企業組織中,一個壟斷的卡特爾(Cartel),受到參加企業互相監視,同時懲罰違背協議者,而此種成本通常很高。在聯合勾結時,每一家廠商都希望其他人遵守協定,但他自己卻可以偷偷減價以擴大銷售。若每家廠商都如此想法,也都這樣去做,那麼聯合勾結行為就會自己瓦解。在台灣,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百貨聯合小組」,當換季拍賣時,各家公司往往爭先恐後地破壞協議。
五、生產力的衡量
這是史蒂格勒在1947年所從事的研究,如今廣受重視並應用的「總因素生產力」和「技術進步的衡量」課題就是這種研究,可見史蒂格勒的先驅性。
六是「經濟規模」的衡量課題。這也就是所謂的「存活」(survivor)法,在史蒂格勒那本《產業組織》書中有完整的闡述。規模經濟是探索廠商的最適規模問題,如果生產過程中有明顯的規模經濟現象,則廠商的規模必定會朝此集中,而離此規模愈遠者,會喪失競爭力而丟失市場。因此,在一段長時間內,能生存下來的或成長較快的廠商,必是生產效率高者。如果觀察這些廠商所處的規模,便可間接推知該產業的生產是否有規模經濟現象。史蒂格勒的研究並不排除生產規模小時也是有效率的經濟,於是規模經濟的討論,乃從最適規模的問題,轉向「最小有效規模」的問題,這種存活法則的研究法,引發了一連串的研究。
七、產業組織理論的實證研究
史蒂格勒在這方面的最有名作品,是對寡佔市場拗折需求曲線的反證,一方面指出該理論與事實不符,另方面又指出,尚有許多其它因素使價格具僵固性。在推翻該理論的同時,史蒂格勒還發現有價格領導的現象,這在往後的寡佔理論中有其重要地位。
除了上提的學術貢獻外,史蒂格勒在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也有極高成就,這也是他自博士論文就開始的研究領域。他對房租管制、最低工資率方案的批判也時常被引述。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政府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非常著重實證。史蒂格勒之所以重視這一點,乃因他深深體認「拿出證據」之後才能大聲說話,也才可以避免特權、利益團體的左右。因此,對於1960年代許多數量分析技巧的出現,史蒂格勒在〈經濟學家和國家〉這篇講詞裏,很興奮地比喻說:「數量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砲代替了傳統的弓箭手。」他更進一步的指稱:「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所謂的李嘉圖、傑逢斯或凱因斯的理論革命,比起數量越來越強大的數量化的牽聯之廣,只能算是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它黃金時代的門檻,不!我們已一腳踏進門內了。」就是由於有此體認,史蒂格勒在該文的末了,這樣寫著:「我對於我們這一門學問的光明遠景感到無限地欣慰。……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學,證明了我們的數量研究,無論在影響力、在小心翼翼的程度,或在嘗試的勇氣上,都大大地增加了。我們日漸擴展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將無可避免地、無可抗拒地進入公共政策的領域,並且,我們將發展出一套制定明智政策所不可或缺的知識體系。爾後,我相當明確地希望,我們將會變成民主社會的中堅人物和經濟政策的意見領袖。」
史蒂格勒自己舉出十本代表性書籍,其中,《經濟學佈道家》(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 and Other Essays, 1962)和《人民與國家》(The Citizen and the Sates: Essays on Regulation, 1975) 屬於通俗性著作。這兩本書都是對公共政策作實證研究的成果之結集,都是史蒂格勒將艱澀的學術理論深入淺出引介,並且化約成政策建言來影響政策決策。要以實證資料揭露公共政策的真相也並非純就資料、數據硬湊而成,最根本的原則必須有堅強的「理論」作基礎,亦即必須本身擁有正確的觀念,當然也必須具純熟的邏輯推理。這又與時下流行的「務實」歪理大異其趣,而沒有理論作基礎的政策有如無根的樹。理論也者,實際現象的簡化,旨在使問題易於分析。因此,理論是用來解釋現象的,我們不太可能得到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理論都隨時準備要被某一現象所否定、推翻的,如此也才不斷會有新理論的出現,這也就是科學進步的表現。所以,理論沒有對錯,只有「有用」或「無用」的區別,能解釋現象的理論就是有用,否則就是無用的理論,但我們卻不能說它是錯的。沒有用的理論或可加以修正變成有用,或因修正成本太高而被新理論取代。
雖然理論很重要,但要將某一理論通俗化的引介,若不是功力夠,以及具有熱誠,否則根本不可能。史蒂格勒兩者皆備。《經濟學佈道家》就是這項工作的一些成果之結集。傳布經濟學理的工作是否類似佈道家的行為?史蒂格勒對此有嚴格的定義,而且強調該行為涉及「道德」層面,或者是與「價值判斷」關係密切。就這一點來說,與基本「實是性」(Positive)經濟學似乎扞格,但卻是公共政策所必須的。不過,史蒂格勒認為,經濟學家並不抱持某一套具有說服力的道德體系,但卻也能廣泛地、容易地扮演政策批評家角色。原因在於批評錯誤時並不需要道德體系,只要是受過良好訓練的政治算術家就可以了,畢竟我們是活在一個老是犯社會性錯誤的世界裏。問題是,決策者真的是那麼愚蠢,竟然一而再地犯錯?當然不是!因為對那些制定和支持「錯誤」政策者而言,那些錯誤政策並沒有錯。這也就是以「自利」原則所可以良好解釋的現象。
《人民與國家》則是史蒂格勒將十五年中對「政府管制」這個問題思路歷程的文章之結集。他認為,傳統上,經濟學家是利用經濟理論,來分析政策中的特定問題。如果經濟學家發現競爭市場未能有效地解決問題,他就建議由政府來擔負解決的責任,但他卻從未將市場和政府的相對效率做一認真的比較。若競爭市場能適當地解決問題(史蒂格勒在1946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的〈最低工資法的經濟分析〉一文,是個相當典型的例子,此文並未收錄在本書中),則經濟學家又會表現出對於政府干預的痛恨。經濟學家並未真切地體認到,最低工資法的訂定其實並非基於一種罔顧是非的善念,而是基於特定區域和某些工人階級實際上的慾望和需索。
這本書有幾個研究是史蒂格勒想要跨越正統經濟理論的疆界,而更確切地評估若干已被實施的政策之效果。此一系列研究中的第一項是史蒂格勒和克萊爾·佛里德蘭(Claire Friedland)研究了政府公共服務委員會管制電費的成效;第二項研究則在探討證券交易員會(SEC)評估新證券的做法之效益,主要是想要知道購買這些新證券的,是否因SEC的評估而受益。史蒂格勒認為,對一項管制政策所「標榜」的目的進行研究是相當有用的,迄當時,美國許多人都對公共政策所造成的實際效果進行探討,而且已蔚成風氣,他對他的這些論文對這種發展有所幫助,其感欣慰。
根據史蒂格勒的研究發現,政府對電費或對公用事業股票投資報酬率之管制,效果都不大;購買新證券的人,也未能從SEC的評估中獲得多少好處。那麼,我們就不能不問:政府為甚麼要採用這樣的政策?為甚麼要堅持這樣的政策呢?
在研究過許多公共政策的實際效果後,史蒂格勒深深以為,光說那些政策不彰或導致反效果的公共政策(如最低工資法)是錯誤的,並未能深入問題的核心。一項政策不但被採用,而且行之有年,甚且廣被各州採用,這樣的政策不可能有效地被描述成一項錯誤,畢竟最後得到好處的團體是知道此種政策的真正效果的。而我們說這些政策是錯誤的,只不過是因為我們不了解它,史蒂格勒就認為,政府管制電費的主要受益者是工業和商業用電的大戶,這在他們的文章中確實有客觀證據的支持。
順著這個思路,我們就很容易想到一個管制性政策的立法市場,它當然是一個充滿政治意味的市場。某些產業、職業團體能從政府優惠(如補貼、限制新工廠加入,以及價格管制等)中獲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好處,這如同某些產業能自卡特爾(cartel)組織中獲得較其他產業更多的好處一樣。此外,有些團體無論藉著票源或金錢方式,都比其他團體更能運作其政治力量。一旦高收益加上低成本,我們自然可預期很快地就會有強力的政府管制。
針對政府的管制政策進行研究,使得經濟學家從「改革者」的角色變為政治經濟學鑽研者,史蒂格勒認為這種改變是有利的。畢竟除非我們能了解我們的社會「為何」要採用某些政策,否則很難對如何改變這些政策提出有效的議。事實上,有些改變(如自由貿易的推行)很難不牽涉到全盤政治體系的重組,而我們又不知如何描述此一理想的政治體系。經濟學家務實的責任感,以及政治界本身保守的心態,兩者皆構成我們在做政策建言,必須知道有所節制的理由。
史蒂格勒表示,這不是說我們應該、或必須在解開所有政府管制過程之謎底前,放棄一切的政策建言。畢竟對一項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本身就有它影響輿論和政策的能力。而認為經濟學家能以快速、優雅且日益正確的方式,為社會提供各種複雜的資訊,即可對社會有所交代,史蒂格勒覺得這種觀點無可厚非,但他認為應該更進一步,因而他也在這本書的第十章中,提出如何強制施行法律的問題。他的基本假設並不是說傳統經濟理論對研究管制毫無幫助,相反地,若理論能直接應用到對管制過程的了解,必能使我們獲益良多。
對於史蒂格勒在《人民與國家》書中的「管制經濟理論」,我在1989年6月、1992年8月和12月,分別在香港《信報財經月刊》和台灣《工商時報》,以及台灣的《中國時報》,發表三篇回應文章,題目分別是「經濟自由的迷惘」、「從護士荒談證照制度」,以及「本末倒置談技術證照制」。
經濟自由的迷惘——經濟管制的迷思
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教授,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論文集《人民與國家》中的〈論自由〉一文裏,感慨的說:「……如果我們要強迫一個二十二歲的典型美國青年表態,他會告訴我們,某些對於自由的侵犯是不可容忍的,但是,這些侵犯通常是來自政治和社會的範疇,而非來自經濟方面的。言論自由不應受威脅,少數民族也不應受到歧視。但對消費者的經濟管制沒有引起任何嚴重的抗議,而這位年輕人甚至準備接受更多的消費者管制。」這些話意指,一般人民不能忍受政治和社會方面的不自由,但卻獨獨對經濟方面的不自由甘之如飴。想想自己、看看周遭人民的反應,史蒂格勒的確說對了。
職業證照普遍存在
環顧四周,最顯而易見的侵犯經濟自由例子是「職業的進入障礙」,這可表現於「職業證照」的普遍存在上。
我們知道,要到學校教書,必須符合教育主管機關訂定的某些條件,要成為醫生、律師、工程師,以至於想當的士司機,都必須通過政府所舉辦的考試,而這些考試也都必須經過一定的訓練才能通過。對於這些舉措,絕大多數的人會舉雙手贊成,因為這些職業都涉及專業技術問題,必須具有某些必要的「能力」才可以擔當。沒錯,我們是一貫接受了這樣的一種信念:沒有人可以不需經過相當的訓練,就有權從事理髮或行醫。為了保護他們的服務對象,亦即保護勞務的使用者(消費者)得到某種水準的服務,對這些職業從業者的資格限制是合理的,因此,基於此種神聖的動機,對於職業的資格限制當然是必要的。這樣一來,很少有人會去想:對職業的限制,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畢竟,擇業的自由是關係到「意願」和「具有能力」去得到某種職業必備知識的自由,試想:一個在心智上和身體上都不適合的人,當然不具有駕駛商用客機,或其他任何飛機的天賦權利。這實在不應該要有事前的門檻限制,這些人往往不會去選擇從事此種職業,因為事實上很難勝任,除非他(她)花下許多成本,費了許多苦功終能成事,但即使如此,也得視消費者是否敢信任!
不過,史蒂格勒告訴我們:「我們當然不能說,生來腿力不好或雙腳有毛病的人,無法選擇運動為職業是被剝奪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只能說:一個人若能達到社團所訂立的技術水準,才有權利去試試該種行業。」問題是:技術標準怎麼訂?由誰來訂?而由個人自由的立場來講,為甚麼個人有必要去遷就這些標準呢?答案是:一般說來,或至少在一些大家所認可的情況下,個人被認為沒有能力來設定一個適當的標準,社會上多數的個人,往往被認定無法辨別好的外科醫生和屠夫之間的差別、無法分辨好的律師與冒牌貨、甚至於不能區分一個能幹的水電工人和笨拙者之間的差異等等。因此,個人擇業自由的受到侵犯,毋寧是值得忍受的。
消費者不願冒風險
我們知道,賦予某個團體訂定進入標準的權利,實際上會形成「特權」,撇開容易出現受賄、舞弊這些由特權生成的「貪污權利」所帶來的壞處不談,就只限於某些夠資格者才能做某種職業而言,供給量就受到了限制。於是,經由簡單的經濟學供需原理,勞務的價格就被抬高了,最明顯的例子是「醫藥的特許」;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沒有醫生的處方不能買藥,事實上就是昂貴的同義詞。對於醫藥特許缺失的剖析,弗利曼早於一九六二年就在《資本主義與自由》這本書裏特就這項最被認定應受管制,必須有醫生、醫藥職照的事項,痛快淋漓的批評了一番。
儘管有這些批評在,但因有「品質」這個因素當守護神,而且社會上不認為一個消費者擁有犯大錯的權利,因而一般人對於個人在這些方面的選擇自由受到限制,也是認為值得的。其實,人們不能僱用受訓較少、但收費比較便宜的醫生,也並不覺得自由已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呢!
依照消費理論,個人在限制條件下,追求滿足的極大,按理說,選擇的範圍愈大、滿足也會愈大。因此,如果像擇業的自由這種自由度愈大,個人的滿足也就會愈大,因而個人應該樂於追求經濟自由的擴大。然而,事實卻不然,道理何在?原來,問題出在「資訊」上,消費者對於未知事物缺乏信心,不願意太冒風險去嘗試,他寧願犧牲掉某些自由來換取安全,這也就是消費者保護運動之所以受到消費者普遍歡迎的原因。當然,這也給予管制者順理成章的施行管制之正當理由了。
對於這種保護消費者的自明之理,一九七0年代初期,曾擔任過尼克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的芝加哥大學教授佩爾斯曼卻提出了石破天驚的不同看法。他以經濟學方法,對於美國一九六二年的「藥品修正法案」作實證分析。該修正案係因應一九六一~六二年泰利竇麥鎮定劑導致畸形胎兒的醜聞,在消費者保護團體的要求下,對於允許新藥品上市的條件,增加了許多新規定。製藥商不但需要顯示產品是「安全的」,而且尚需證明藥是「有效的」,甚且,該修正案也不再規定食品藥物管理局必須在一定期間內,對新藥品的許可作成決定。
保護過度反成障礙
新修正案的原意在杜絕不良藥品的出現,也希望能免去藥物太浮濫所形成的經濟上浪費,立法目標不但要增進消費者的安全,也要讓消費者免於購買缺乏真實醫療價值的藥品。對於這種善意,佩爾斯曼以有利於新立法的假設為基礎進行研究:如果藥品市場沒有管制,則分辨有效和無效藥品,得靠醫生和病人透過「試誤」的過程來決定。在經過相當短暫的一段期間後,所有無效的藥品便會受到排斥,以經濟術語來說,就是對這些藥物沒有需求了。
如此說來,新的修正案是在免掉消費者試誤過程的學習成本,而將該成本轉至食品藥物管理局去負擔。為了證實修正案是否達到目標,可以比較一九六二年新修正案通過前後,新藥的供給和需求變化:若立法有效,則新藥的供給和需求不會在上市後逐漸遞減。佩爾斯曼的實證顯示,修正案通過後,無效藥品的出現比例並未減,亦即,使用新藥的學習成本未減,經濟浪費也沒少。更遺憾的是,每年上市的新藥方約少了一半,新藥上市時間平均延後四年,並且所有的藥價都顯著地上升。再據佩爾斯曼的估計,修正案非但未能改善消費者所用的醫藥品質,反讓他們每年多花等於六%的租稅。這項立法只有兩種人得利,一是權力和職責都擴大了的政府官員,二是受保護而免於競爭、以至缺乏創新的製藥公司。
由於醫藥的管制最能被大多數人認同,但卻也如此被證明不但不能如人意,反有不良結果產生,遑論其他受限制的經濟自由了。可是,要使一般大眾接受這種說法,只怕不那麼的容易,畢竟,大多數人還是偏好被保護的!此由我們社會早已通過實施「公平交易法」和「消費者保護法」可見一斑。
從護士荒談證照制度
在一九九二年八月,那些台灣曾赴公立醫院就診,且不幸又需辦理住院,甚至需開刀治療者,一定嘗受到吃閉門羹的滋味,原因不在醫師缺乏,也不是病床不夠,而是護士不足。這種現象在高普考舉行的期間更是明顯,公立醫院異常冷清,護理人員大都赴考去了。為了甚麼?當然是為了取得任用資格,或以術語來說,是要得到「證照」。
證照制度的出現是出於「善意」,為的是保護消費者的權益,生怕消費者不查,或無能力去分辨產品的好壞,一旦誤買不良品,花錢事小,賠上健康、甚至連生命都丟了。於是「事前」的保護必須周到,一定得「保證」只有優良品才可面世讓消費者來選購。對於這樣的說詞,相信反對的人很少,因為個人的知識和能力有限,對於「無能區」,若有人或某個團體幫我們消除,怎會不好?不過,這種立意良好的做法,卻有非常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誰有資格來幫大家把持「品質保證」的關卡?如果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應是屬於「共用財」的範圍,因為幾乎每個人都想當「搭便車」或「享用免費午餐」者。於是這項任務就落在為民服務的「政府」身上,縱然政府人員都極優秀,但面對無數的無能區,那有這麼多人手負責?若要勉力為之,濫竽充數就出現了,如此,品質能保證嗎?一旦品質不能擔保,民眾又過份安心的相信,不是更會受到傷害嗎?其次,即使政府夠格來篩選,這種優秀人力勞務的成本誰來支付?這種成本是否低於競爭市場裏的成本?如果政府機構無力負責,必得委於某個團體來做,到底要託付給誰呢?又如何判定這些團體的能力呢?第三,類似「證照」的行為,最被詬病的就是形成「人為獨佔」。就連最無異議,最具專業,以及與人體健康最有密切關係的「醫師執照」,在這方面所產生的不良副作用,就算在先進國家也有出色的研究予以證實呢!
其實,信用、品質保證,以及品牌等等,由民間人士和團體自己努力建立應較實在。由政府所賦與的獨佔特權,非但品質無法保證,且因供給受限,至少價格一定高昂。
回到護士資格的取得,其技術真的高到必須嚴予管制嗎?公立醫院護士的勞動條件是否由於必須通過雙重關卡,多了一層限制,因而低於一般醫療機構的護士?此種制度性的限制所導致的供需失調,使醫療資源閒置及病人受害,如何才能儘快去除?銓敘部、教育部、考試院等等有關單位是否應儘速協商出良方來?何不乾脆將限制解除呢?
本末倒置談技術證照制
一九九二年十月,台灣教育部召開了北中南三區座談會後,做成這樣的結論:應立法規定各事業單位聘雇一定比例的技術人員,且持有證照者得調高薪資及獲陞遷資格,其目的在「落實證照制度」。而教育單位調查證照制度難以推行的原因,發現技職學校學生參加技能檢定的意願不高,這個現象又導因於社會不重視「技術士證」的持有與否,於是造成惡性循環。
技職學校學生並不熱中參加技能檢定,其癥結被認為在於社會不重視「技術士證」。教育部於是欲以立法「強迫」各事業僱用「一定比例」的技術人員,並且還要命令業者調升持照者的薪水和職位。這種對事業者經營權進行「父權式」干預的做法,令我們想起不久前內政部強迫各公民營機構必須僱用「一定比例」的身障人員,兩者異曲同工,而這一次的做法更為不堪。由內政部該項政策所引發的紛爭,以及窒礙難行的困境,我們難免擔心教育部此舉若勉力實施,又會落得灰頭土臉,若是無法順利進行而中途腰斬,只是公權力再次受到損傷,使政府政策草率決定又添一例而已;若是不幸真的立法蠻幹到底,原本已經慘澹經營並處於飄搖期的事業主,更是雪上加霜,甚至於整個台灣經濟都將受到莫大的戕害,實不可等閒視之。
技術的提升本是一件好事,業主能夠僱到技術良好者也是美事一樁,如果「證照」真能實際反映技術的良窳,固然也能減低業者的「蒐尋成本」。問題是,果若證照真能代表技術水準,又何必煩勞政府以「法令」來強迫業者用之?業者不擠破頭去搶人才怪呢!如此一來,持有證照者哪裏會有薪水不調、職位不升之理?因此,必須勞動政府以法令干預業者,強迫業者對持有證照者特別照顧,其中必有文章,亦即目前的「證照」只是虛有其表的一張卡片或紙張,並不是技術水準的同義詞,因而遭到社會的遺棄,也當然吸引不了莘莘學子去辛苦的參與檢定取照了。
問題其實很明顯,一定是目前的檢定不合時宜,而通過檢定而得到證照者,禁不起事實的考驗,其價值遂不被事業主認定。而在殘酷事實的現狀下,學生不去參加檢定不是很「理性」嗎?因此,根本之道是,有關單位應反省為何現今的技能檢定如此不堪,趕緊找出癥結,對症下藥,以提升品質來得到社會認同,進而吸引學子們自動自發踴躍參與檢定,在取得證照後才得以飛上枝頭作鳳凰。哪裏知道教育部竟想以「便宜行事」的鴨霸方法,希望藉「法令」強壓業者就範,除了將濫用公權力外,還將拖累台灣經濟,希望有關單位趕緊煞車,勿本末倒置,一意孤行!#
--------------------
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