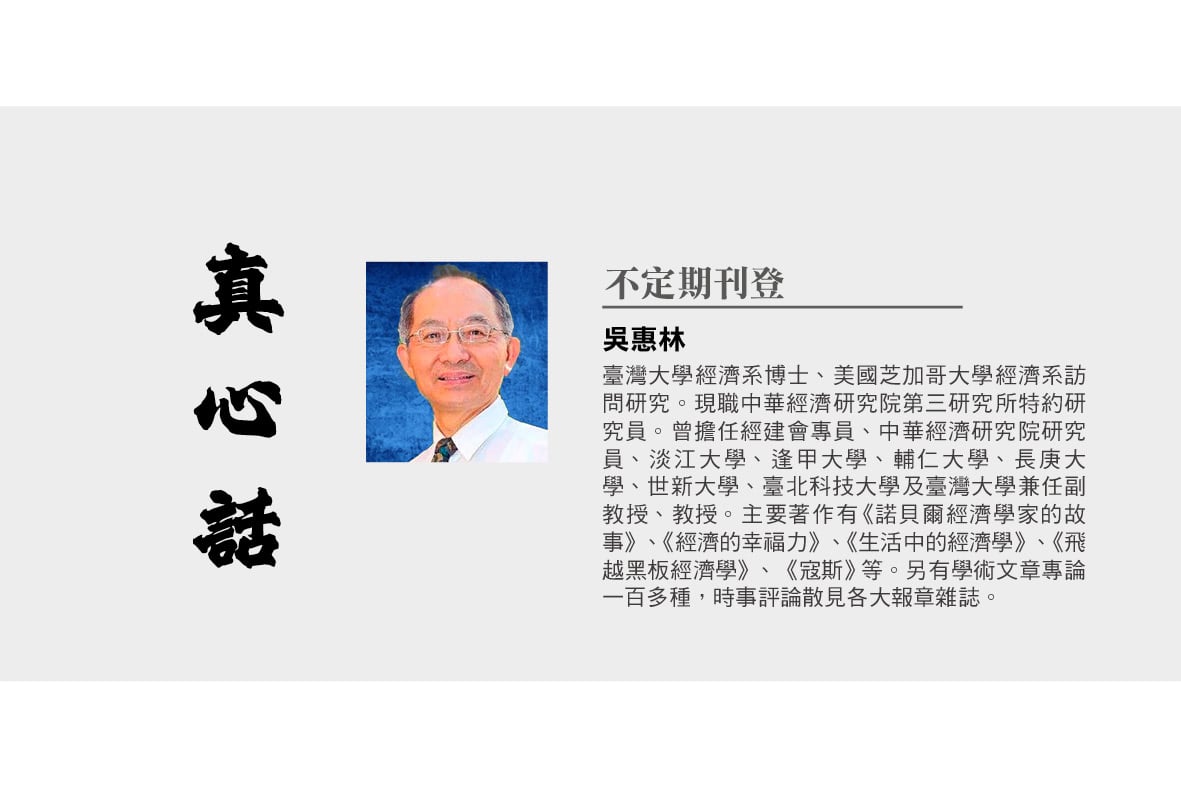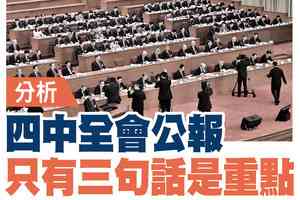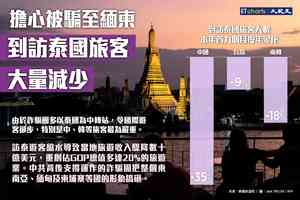1958年史蒂格勒返回母校芝大任教後,與弗利曼等學者將「芝加哥學派」這個招牌擦得其亮無比。究竟「芝加哥學派」是甚麼?有不少說法,也有專書出版,而史蒂格勒這位當事者又是怎麼看的呢?
史蒂格勒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蒙貝勒蘭學會(Mont Pelerin Socity,簡稱MPS)首次聚會之前,亦即1947年4月之前,經濟學領域中尚未出現芝加哥學派這個名號。1930年代時,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與其它地區是有些許差異,但大多數主要的大學也都能這麼說。
芝加哥學派的醞釀成形
當時,奈特對政治行為的道德與智識意涵感到懷疑,尤其對中央經濟計劃更不以為然,但他對競爭經濟的倫理基礎也同樣嚴厲批評。賽蒙斯在1934年出了一本有名的小書《自由放任的實是計劃》(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 Faire),書中倡導自由放任,但那是很奇怪的自由放任。他居然建議電話和鐵路之類的基本工業應收歸國有,理由是管制的成效不彰。賽蒙斯極力促進所得稅的公平政策,以及對廣告之類的商業活動訂定詳細管制。他的大部份計劃幾乎是社會主義與私人企業資本主義和平共存。不過,在貨幣政策上,他認為必須遵循法則而不是採用權衡性的操縱,此想法深深地影響了後來的芝加哥學派。具體而言,他主張該法則應是一個綜合性物價指數的固定比例,很明顯的,該法則就是後來對貨幣供給增加率建議的源頭,該建議倡導貨幣供給應每年增加3%或4%。
另一位重量級人物是范納,他有19世紀的自由傾向,反對教條式的或簡化的或「極端的」立場。其他芝大教授在政策偏好上差異極大,譬如,道格拉斯贊成政府在經濟層面應扮演吃重角色;李嵐(Simoon Leland)在租稅上持傳統意見;米立斯是個古板的勞動經濟學家;敏斯(Lloyd Mints)只寫有關中央銀行政策的文章;休茲潛心於數學和統計的結合;藍格(Oskar Lange)則為社會主義者。
范納和他當時的學生,曾宣稱當時並無明顯的芝加哥學派之名稱或學說形成。史蒂格勒也沒發現在1950年以前,經濟學界有認知芝加哥學派的跡象。不過,1960年代以前,經濟學界已廣泛同意芝加哥學派確實存在。張伯林(Edward Chamberlin,1899~1967)在1957年出版的《朝向更一般化的價值理論》(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Value)一書中,就有專章介紹芝加哥學派,他認為該學派的特色是「熱中攻擊獨佔性競爭的理論」,還以「反獨佔性競爭的芝加哥學派」稱之。而米勒(H.L.Miller)可能是撰寫第一篇完整介紹芝加哥學派及其中心思想的論文者,該文刊在1962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期刊》。到那時芝加哥學派算是正式成形,不但廣受認同,也廣遭貶抑。
史蒂格勒認為芝加哥學派有兩大中心論點:一為政策立場,二為研究經濟學的方法。政策立場是芝加哥學派比較被認同的特質,而1946年回返芝大的弗利曼, 很明顯是這些政策觀點的主要建構者。他在1946年以前甚少談論經濟政策,只有一些在二戰期間探討通貨膨脹的文章,以及1946年和史蒂格勒合著的一本小書《屋頂或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該書旨在抨擊「房租管制」。
回到芝大後,弗利曼有了急遽的轉變,他致力於三方面的工作,也形成芝加哥學派的基本信條。第一、他使已暮氣沉沉的貨幣經濟學重現研究生機,除將貨幣數量學說加以整修外,還擴展其應用範圍。不僅用於研究經濟行為,而且對凱因斯學派發動強力攻擊。第二、弗利曼極力為自由放任的政策衛護,同時提出重要的新政策建議。第三、他以多種重要的方法發展並採用現代價格理論。
在駁斥凱因斯學派經濟學方面,弗利曼成功地驅散凱因斯教條,有效地對抗在美英兩國大多數總體經濟學家的反擊。他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實證法則,亦即,貨幣供給的變動與全國貨幣所得的變動息息相關。在政策討論中,貨幣角色的重要性無疑地應主要歸功於弗利曼的貢獻。
弗利曼所強調經濟運作中,貨幣存量變化的重要性,的確是1930年代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的根本信念。他不只承繼這項傳統,還加以發揚光大。弗利曼做了很多實證研究,紀錄了貨幣在美國經濟生活中強大的歷史角色,同時也應用此理論作為批評凱因斯理論的利器。他以高超的技巧進行這些工作,他的思路極為明晰且反應很快,常能在熱烈辯論中,完全掌握適當的論點,使他在面對辯論或打筆仗時,成為難纏的辯論者。弗利曼是一個傑出的實證工作者,隨時準備懷疑自己的信念就是某個問題的關鍵,依據實證資料進行最精巧的分析。弗利曼很有本事引發對手憤怒,從而花費很多精力替他的觀念打廣告。史蒂格勒覺得,弗利曼作為辯論者的唯一瑕疵是,他的勝利往往往是短暫的,被他打敗的對手多會偷偷地自言自語說:「幾天之內,我一定要想出來怎麼答辯。」
不過,史蒂格勒認為弗利曼不是個擅耍詐術者,而是相信自己所說的,同時也只說他相信的。當他倆1957-58年在史丹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共事時,有一次兩人拍檔進行一場娛樂性辯論,對手拍檔是梭羅(Robert Solow,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瑞德(Melvin Reder)。辯論主題是「解決了:犯罪划不來。」當時史蒂格勒為他們正方提出一個有趣的、但可能有誤導性的經濟論點,可是弗利曼拒絕採納,說「就算是開玩笑,一個經濟學家也不可能誤用經濟分析。」由此可見弗利曼是多麼嚴謹,史蒂格勒要大家想想看,我們每天不知道要遇到多少個正式場合的誤用例子。
幾十年來,許多有份量的貨幣經濟學研究都出自芝加哥大學。其中,弗利曼的著作最具代表,而他與安娜‧許瓦茲(Anna Schwartz)合著1963年出版的《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尤其重要,可以說芝加哥經濟學的貨幣面就是弗利曼創造的。
在公共政策上的著作,讓弗利曼成為家喻戶曉的的人物,196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以清晰和諸多的案例闡述自由經濟,銷量歷久不衰;1980年弗利曼與其夫人蘿絲(Rose)合寫的《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一書更為成功,還製作成同名的十集電視節目,廣受歡迎。弗利曼應各界邀請發表了無數次的演講並參與諸多辯論,他還擔任數十年《新聞周刊》(News Week)的專欄作家,使他在公共政策方面更為人知曉。
史蒂格勒特別舉「教育券」和「負所得稅」兩個例子來說明。弗利曼建議使用教育券,讓父母有幫他們的子女自由選擇學校的權利,如此也可將競爭導入公立的中小學。方法是:每個兒童的父母都會收到一張教育券,約是等於一位學生在公立學校平均一年的費用,該教育券可在任何品質合格的公私立學校使用。至於負所得稅,是針對低收入戶,以現金直接補助取代現行的一大堆公共福利計劃,如失業救濟金、食物券、房租補助、健保補助等。
這種做法對家人的幫助較有效,因為現行的很多國民住宅與其它福利的受惠者是中產階級。更重要的是,負所得稅的收受者會有選擇的自由,例如選擇更多的食物或醫療而減少住宅的消費。很多人反對這個建議,主因是他們認為家人不會善用金錢。史蒂格勒和弗利曼都不擔心會這樣,史蒂格勒擔心的是,負所得稅不但不能取代既存的眾多公共福利政策,反會成為新增的一項福利。
史蒂格勒認為,教育券和負所得稅兩者展現了弗利曼以新穎和啟發性的態度探討公共政策的能力。雖然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一樣,都有很多意志不堅的分子,但弗利曼的反應是睿智的,且其建議不迂腐。史蒂格勒指出,謹慎且持續使用現代價格理論,是弗利曼有著重大貢獻的第三個領域,其源頭並非弗利曼,而是范納在經濟理論的著名課程,而弗利曼的主要貢獻是,嚴謹地呈現價格理論來指導數個世代的學生如何使用。
芝加哥學派的重要成員
史蒂格勒本人是芝加哥學派的要角,是1958年才回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服務,上文已提過其間的轉折。當時有許多個各擅所長的新舊朋友得以形成「學派」。艾倫·達瑞克特在1947年接替賽蒙斯在法律學院的教職,是芝加哥學派的要角,他和史蒂格勒在1947年蒙貝勒蘭學會(MPS)成立大會時首度聚會,之後成為密友,且是相當親密的朋友。史蒂格勒認為達瑞克特是個有禮貌、有修養的紳士,思想敏銳且對問題都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
第二位是凱塞爾(1975年就英年早逝),史蒂格勒說他有著活潑的性格–直腸子,有時稍嫌魯莽,天真又夾雜一些頑固。凱塞爾出身貧寒,史蒂格勒記得有一次他們正在傳遞一大堆佳餚中的美味餡餅時,凱塞爾感嘆說,他早期不吃餡餅是因為吃不起,後來不吃是因為它卡路里太高,所以真正吃餡餅的日子少得可憐。史蒂格勒覺得凱塞爾的懷疑態度有點病態,而凱塞爾曾告訴史蒂格勒一個故事:有一次凱塞爾在旅途中得了盲腸炎,在被推往手術房碰到醫生時,詢問醫生的證件來自何處。史蒂格勒反應說:「天哪!凱塞爾,你對醫生的證件了解多少?」凱塞爾回說:「不太多啦,只是他如果趾高氣昂,我就取消開刀。」還好的是,那個醫生並不高傲,凱塞爾欣然接受開刀。凱塞爾經常企圖做一個真正的經濟人,對所進行的事都保持理性。因此,凱塞爾的往來銀行是在密蘇里州,因為他找到一家當時少見的不收服務費的銀行。
凱塞爾也會因為很少收到其它學校的任教邀聘,基於自尊,變得情緒化的沮喪。史蒂格勒強調,凱塞爾真的是一位很好的經濟學家,其專長是在健康經濟學方面,早期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醫療學會對猶太裔醫生的敵意是起因於猶太醫生有殺價的傾向,該文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
第三位是寇斯。他是1964年來到芝大任教的,是非常有名的「寇斯定理」的作者,而「寇斯定理」這一名詞則是史蒂格勒冠上的。寇斯非常精通英文,崇尚自然隠居,史蒂格勒記得他好像電話都沒裝。寇斯是個慧黠且文雅的學者,對時髦思潮免疫,包括經濟思想在內。史蒂格勒說亞當·史密斯在一小段文章中提過,英國是個充滿小店主的國家,而史蒂格勒曾仿傚亞當·史密斯的口氣對寇斯說,就他的獨立性和能力言,至少是個大百貨公司所有者,這就是寇斯不加入芝大教授們對經濟生活中的獨佔角色採取絕望的誇張見解有感而發。
第四位是路易斯(H. Gregg Lewis),他是當時經濟學系的支柱,不僅解決系裏困難的行政事務,也化解學生課業上的難題,同時始終重新建構勞動經濟學的現代形式。第五位是羅瑞(James Lorie),他是現代財務經濟學先驅,史蒂格勒說羅瑞是他所見過最有譏諷本領的人,而史蒂格勒本人其實是最具幽默譏諷本領者,能被他點名稱讚,可見羅瑞的不同凡響。第六位是鄧塞茲(Harold Demsetz),他是史蒂格勒的好友兼同事,但他後來離開芝大到加州去。第七位是特爾色,他擅長以高超的技巧來反駁世俗人云亦云的常識。第八位是佩爾斯曼,他曾是芝大優秀的學生,之後擔任芝大教授,其學術生涯多彩多姿且富創意,史蒂格勒說就如同他在服裝上變化一樣。
第九位是波斯納,是個聰慧的律師和卓越經濟學家。他幾乎是獨立開創了法律經濟分析領域,其驚人的能力使他開創了一個令人羨慕的教授生涯,而且發展出擔任聯邦高等法院法官的另一個生涯。其他還有擅長公共財政和經濟發展的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著名的「哈伯格三角形」就是他創建的)。農業經濟和經濟發展專家強森(D. Gale Johnson),以及農業經濟、經濟發展和人力資本專家舒爾茲(T. W. Schultz,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
史蒂格勒特別提到舒茲(George P. Shultz),他原先是以工業關係的教授應聘,後來由於正直判斷力佳,行政能力又好,很快地被商學院教授說服出來當該院院長,後來走入政界,擔任過尼克森總統的勞工部長、財政部長,以及國務卿。若他未踏入政壇,必然會在學術界或企業界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以上這些芝加哥學派成員都是1988年以前有所成就的人物,當時也出現了芝加哥經濟學的新領袖群,帶給芝加哥學派新的研究方向。史蒂格勒認為貝克(G. S. Becker)和盧卡斯(Robert Lucas)兩人最為重要,而羅森(Sherwin Rosen)和拉季爾(Eduard Lazear)也很不錯。
貝克是一個極具原創力的學者,在擴大經濟學的應用層面上,貢獻卓著,他的博士論文名為《歧視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他是第一個將經濟分析應用於種族、性別和其它形式的勞動市場歧視者,從而成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概念之發展的領袖人物。「人力資本」指的是一個人的天賦與技能的價值,以及創造那些價值的投資型式。之後,貝克重振了犯罪與懲罰的經濟理論,並且開創了家庭(結婚和離婚、子女人數和品質、利他主義等等)的經濟理論,他在1981年出版了《家庭論》(A Treatise on the Family)這本耗費他畢生心力質量併重的曠世巨著。貝克獲得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盧卡斯是總體經濟學裏「理性預期理論」的先驅,該理論的精義是在鑑別政府和個人的行動不會令經濟行為人感到驚訝。例如,當強大的通貨膨脹快發生時,聯邦準備銀行通常會賣公債給商業銀行,從而整個金融圈就會預期此種行動,故會在政策尚未成形前,就採取適當的行動,使自己免受其影響,於是政府政策就無效。這個理論對大多數的傳統經濟理論,包括凱因斯學派的理論在內,產生了嚴重的破壞力,該理論也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派,挾其嚴謹的學理分析,得到「政府的安定政策,即使在短期也是無效」的結論,不僅將自由放任的主張加以擴充,也等於真正的否定「凱因斯學派的凱因斯」,其所引起的論戰,連綿不絕,而盧卡斯也因而獲得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
芝加哥學派在個體經濟學上的研究
史蒂格勒指出,1940年代末期,探討市場行為的研究有兩大學派的思想,都以哈佛大學為中心。一是由張柏林開創和領導的獨佔性競爭理論,二是由梅森(Edward S. Mason)帶頭的制度性市場學派,重要成員有邊恩(Joe S. Bain)、凱森(Carl Kaysen)和華列斯(Donald Wallace)。
獨佔性競爭理論一直到1950年代末,都對經濟學有深遠的影響,之後則明顯呈衰頹之勢。情況是,許許多多的經濟學家就其中心議題─同級產品(如早餐食用的穀類食品)「之間」的差異(不同品質品味、地點、服務等等)在各行業中相當普遍─賦與各式各樣的面貌,不過,這些研究都缺乏對那些行業之運作給予有趣的實證內涵。因此,該理論只屬於描述性,而非分析性。
在哈佛大學以梅森為首的那些學者,最會製造產業組織領域的博士。每個博士都需提出有些難以理解的產業組織架構,卻不必顧慮其博士論文所探究的產業,是否按照社會認可的方式運作。即使是該學派最具影響力的著作─邊恩的《新競爭的障礙》(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1956),其本質也是主觀的,它並未應用到現代價格理論的精華,也未持續使用現代價格理論。
那時逐漸形成的芝加哥學派傳統,就挑戰這兩大主流的觀點。芝加哥學派的起點是,假設現代價格理論是了解經濟行為的利器,而非只是一組適合教學以及展示人類敏捷心智的優美理論練習。尤其是,該學派學者不再假設獨佔充斥於當代經濟活動中,史蒂格勒認為這主要是受到艾隆‧達瑞克特的影響。芝加哥學派的取向有三個構面:一是經濟生活中追求效率的目標隨處可見,這效率指的是,儘可能以最低成本製造且銷售商品,從而可產生最大可能的利潤。不論是競爭者或獨佔者,都是汲汲營營地追求此目標。許多現象能以追求效率來解釋,但獨佔力的存在卻毫無解釋能力。譬如說,維持轉售價格—商品製造商限制零售商的最低售價—的做法。
傳統理論對這種行為的解釋是,認為製造商以排除零售商的價格競爭,來排除製造商價格競爭的間接壓力;另一種說法是認為此種行為只是起因於零售商卡特爾的堅持所致。由特爾色發展出來的芝加哥學派之解釋,就截然不同。假設有一家折扣商店,在與一家傳統的百貨公司競銷家電產品,如果沒有限制轉售價格,則消費者可以先去百貨公司看貨,然後到服務差、低價的折扣店購買。長此以往,百貨公司就不會再提供各式各樣的家電產品,也不會再提供說明產品性質的零售服務,而家電產品的銷售量就會下降。為排除折扣店搭便車的行為,限制轉售價格之類的做法是有必要的。
另一個例子是廣告。史蒂格勒認為,對1960年以前的大多數經濟學家而言,廣告不過是招攬顧客購買自己廠牌商品的方法而已,而且無可避免地可予操縱。尤其,一般人咸認完全競爭廠商或產業,不會去打廣告。史蒂格勒對資訊經濟學的研究,引發了截然不同的看待廣告的觀念。因為消費者或經濟生活中的任何人,需要大量的資訊,例如:有甚麼新產品可買?哪裏可買到新產品和舊產品(因為商店開開關關)?如何取得品質保證?誰賣得最為便宜?等等。廣告就是提供絕大多數這些訊息的極有效方法,而且不論對獨佔者或競爭的廠商來說,都是關鍵性的做法。
芝加哥學派產業組織研究的第二個主題是:幾乎不可能排除經濟生活中的競爭。就算某個廠商買下所有的對手,新的對手還是會出現。假如某家廠商取得某種可獲利的產品專利,則其對手會大手筆地投資,來開發替代的產品或是不同的生產方法,以便瓜分第一家廠商的利潤。如果政府授予獨佔特權(如電視頻道),則在政治圈就會出現爭食這些甜頭的激烈競爭。
鄧塞茲在分析所謂的「自然獨佔」時,對此論點作了重要的貢獻。這些自然獨佔譬如自來水公司的公用事業,它們有獨家供應某城市所需的權利。鄧塞茲指出,在此情況下,競爭的壓力會在爭取特權的階段感受到。會有很多廠商爭取供應自來水的權利,它們之間的競爭能導引為有利於消費者的福祉。
競爭力量的存在並不表示沒有獨佔存在,也不是說獨佔總是短命的–儘管一百年以來,獨佔確實是短命的。它所意含的是,獨佔地位的取得、衛護、分享和淘汰的過程,遠比獨佔力量的運用來得重要及有趣。史蒂格勒引希克斯(John R. Hicks)的說法:「平靜的生活是獨佔利潤的最佳狀況」,該句話主要是描寫一位偉大的牛津大學經濟學家的生活,而史蒂格勒卻認為也有些適用於市場之情形。
由於芝加哥學派轉向注意效率,以及恢復競爭的強勢角色,這兩股力量削弱了應否以反托拉斯政策對付那些不重要,或暫時性的,或(就垂直結合而論)錯誤認定的獨佔措施的爭論。每一件重大的反托拉斯行動通常需耗時五或十年的工夫,而且原告和被告的總花費會高達數百萬美元。史蒂格勒認為,反托拉斯這種補救之道,應保留用於那些大部份是起源於政府管制的重大且持續的獨佔問題。
芝加哥學派的第三個面向是有關政府(公共)管制的理論。這方面的研究和傳統主流更是不同。原有探討產業、產品和價格的大量文獻,幾乎都在討論應該如何進行管制(這是規範性的分析),而芝大則開始探討管制行為何已出現,以及有何實際效果(這是實是性的分析)。
芝加哥學派的這三個途徑,即轉而研究市場效率,指出競爭壓力普遍存在,以及將經濟學應用於公共管制的形成與效果之研究,對於產業組織方面的文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史蒂格勒說,若說芝加哥學派征服了這個領域,一點都不為過,因為1980年時的經濟學家之著作,已很難找到追隨張伯林和梅森兩大哈佛傳統的痕跡。
展望芝加哥學派
到1980年代末,貝克和盧卡斯兩位是芝加哥學派的新星,他們兩位的研究或新發展,是否能代表芝加哥學派核心思想的延續?史蒂格勒給予肯定的答案。因為每項發展,都將經濟理論持續且一致地應用於過去被經濟學家視為「給定」的制度和行為範疇,即研究生活中難解的事實,而不是研究理性經濟行為的產物。史蒂格勒說,如果在一所大學裏看到像貝克和盧卡斯兩位經濟學家及其後繼者,撰寫否定芝加哥學派傳統的著作時,可就會讓人吃驚了。
史蒂格勒認為,每個思想學派的壽命必然有限,而且通常是短促的。因為它有兩種可能的結果,一是說服其所屬的領域接受該學派的中心命題,一是說服失敗。若是前者,則該學派就沒有存在的理由,若是後者,則該學派將因徒勞和厭煩而結束。奧國學派由1870年存續到1930年,時間相當長,主因是其對手德國歷史學派在經濟學上一直倡行反理論的方法論。而德國學派雖然在經濟學方面沒有永恆的影響力,但因它控制了教育部,間接地控制了教授的聘用,故能持續良久。
至1980年末,芝加哥學派挺立了四十餘年,史蒂格勒認為並非因為該學派堅固頑強,而是因為他的創造力。弗利曼在1970年代中期離開的空缺,由貝克、盧卡斯和公共管制研究群的新方向接替該學派的香火。
史蒂格勒表示,雖然某個學派會打敗其對手,如芝加哥學派於1960年到1980年在產業組織領域獲勝,但勝利不會是永久的。假如勝利的一方固定地以某種新型態進行研究,那勝利也不能持久。例如:研究產業組織的最新發展是,採用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方法。美國東部主要的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年青一輩經濟學家的作品,多屬此類。這些文獻和張柏林學派的經濟學,在精神上高度相關,只是更為嚴謹,但它在實證驅動力或實證適用性上並無相稱的收穫。
一旦一個學派已建構完整,則招募新血將可增強其核心思想,要達成此一目標,可採行招募那些同情該學派觀點的學者方式,但存在著更強大的阻礙招募之力量。就芝大來說,它在過往的兩個學術年代裏,曾對稍低於史蒂格勒輩分的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1915~2009,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梭羅(R. M. Solow,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托丙(Jame Tobin,1918~2002,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及更年輕輩分的巴羅(Robert Barro)、費雪(Stanley Fischer)、霍爾(Robert Hall)、喬根森(Dale Jorgenson),以及沙金特(Tomas Sargent,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等人,提供邀聘函,卻遭回絕。史蒂格勒猜測,這些卓越學者回絕的主因大概是,他們覺得自己將會陷入一個不熟悉的學術環境,致難以適應。史蒂格勒認為他們可能錯了,因為前不久公認的社會主義者藍格就適應得很好。不過,誰也不敢肯定。
史蒂格勒認為,學派的興起通常是因應科學的需要,而非有某些社會契約所創造,也就是說,它們具有一項重要的科學功能—將其所屬學門中,對適當的新研究方向具有共識的學者聚在一起。這個族群為了強化他們對該學門適當研究內容的共識,會以自我批判、多樣的應用、持續的修正,以及與競爭對手不同的研究內容進行激烈的爭辯。要重大改變一個規模完整的學門之走向,幾乎無可避免地需要多方學者的努力。即使是牛頓或亞當·史密斯,要征服已建立相當基礎的學說或方法論時,也需要門徒或同伴助一臂之力。史蒂格勒主觀地認為,芝加哥學派是美國經濟學興盛的一項重要泉源。
(未完待續)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