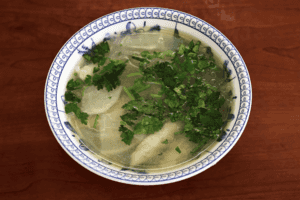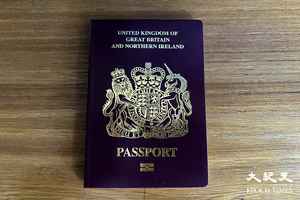連日來,香港發生幾宗嚴重交通事故,當中有不少爭議。九龍灣休班海關以肉身作路障導致電單車手失控撞柱身亡,社會聚焦討論涉事人員是否誤殺;連翔道發生貨車硬憾停於慢線的垃圾車車尾,貨車凌空彈起,司機被困,送院不治,事發後有人將汽車紀錄儀片段上載社交平台,有網民質疑汽車紀錄儀上載者當時是否可以響咹,嘗試提醒貨車司機,減低意外發生的可能性。
沒有人希望發生交通事故,現場旁觀者當時是否較受害人更有能力察覺意外發生,當屬疑問。然而,這個爭議帶出了一個問題:響咹在駕駛中的重要性。
甚麼時候應該響咹,這是駕駛者經常討論的問題。響咹是除了燈號外最重要的汽車溝通方法。一個普遍接受、甚至已經寫進駕駛規則和指引的標準是:響咹不是為了表達個人煩噪不滿,例如塞車以及與交通安全無關事宜,見到熟人響咹有時也會令人側目。響咹是為了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或車輛作出提示甚至警告。換言之,響咹有公民社會社群互助的性質,例如見到前車爆呔卻仍然高速行駛,會響咹提醒。筆者試過在英國燈位停車,後車不斷響咹,我以為與我無關,沒有理會,最終後車司機下車,走到我車旁,把我未關好的油蓋關好。
響咹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有學者為它寫了一部專史。賓夕凡尼亞州州立大學傳訊系教授Matthew F. Jordan的著作Danger Sound Klaxon!: The Horn That Changed History,顧名思義,是圍繞著20世紀初最流行的汽車響咹品牌Klaxon作出討論。擁有私人汽車,當時被視為一種身份象徵;身份的極致便可能是車未到聲先到,所以Klaxon這種外置汽車響咹聲量雖然超過一百分貝,車主們仍然樂意使用。該書作者形容當時車主們的心態:「我不需要把車慢下來,因為我有市場上最大的車咹。」
讀者可能會問,為何那時的城市可以包容這麼嘈吵的車咹?原因雖然複雜,但亦合理:首先,那時駕駛典章制度還未完善,缺乏交通標誌,汽車自行發出警告便是最有效的示意方法,有些地方甚至規定汽車在街角轉彎若不響咹會受罰。更重要的是,城市本身就是充滿喧鬧聲,相比於街上的叫賣聲以及蒸汽火車頭的聲音,汽車反而是噪音較少的交通工具。有種講法認為,汽車出現時,用馬拉動的巴士(omnibus)仍然大行其道,人們會關心馬路上布滿馬屎多於區區汽車響咹。「馬路」一名延續至今,或多或少反映了人們關心的是甚麼。
另一個與「延續」有關的是車咹的音質。該書指出,自20世紀初至今,汽車響咹聲一直沒有明顯變化, 原因是要讓道路使用者一聽便知道是汽車發出的。戰前香港報章報道,有單車使用Klaxon而非單車專用鈴,原因不是其聲音過響,而是會讓其他道路使用者混淆車輛身份而作出錯誤判斷。
二次大戰後,隨着科技發展,汽車數量大增,對汽車的管制亦陸續增加,響咹文化出現大變。雖然不可以再隨意響咹,但司機們有需要時,必須果斷使用燈號和車咹,使用提示和警告。◇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它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
🎯 專題:中共海外升級攻擊法輪功
https://hk.epochtimes.com/category/專題/中共海外升級攻擊法輪功
----------------------
【不忘初衷 延續真相】
📰周末版復印 支持購買👇🏻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