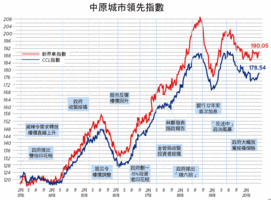前言
前章所介紹的芝加哥學派是引用弗利曼這位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說法,強調芝加哥學派的三大特色:一為將經濟學當做一門科學,稱之為實證經濟學;二為在討論經濟政策時,相信唯有自由市場才能有效組織資源,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事務;三為強調貨幣因素。該章只著重這三種特色的陳述,並沒著墨於其形成過程,也沒有交代芝加哥學派的由來。本章即擬彌補該文的不足,特別參酌史蒂格勒這位芝加哥學派健將,也是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於去世前不久出版(一九八八年,史蒂格勒於一九九一年底去世)的親筆自傳,將芝加哥學派的來龍去脈作扼要敘述。
芝加哥學派的出現1
一般都習慣將奈特視為芝加哥學派的始祖,但身為奈特嫡傳弟子的史蒂格勒有不同的看法,史蒂格勒之所以不認同奈特當頭的一九三0年代即有芝加哥學派,最主要的原因應是基於弗利曼所標榜的該學派三大特色在當時並未能成形,而且奈特本人的主張也與這些特色不完全相同。史蒂格勒指出,奈特固然對中央經濟計劃頗為敵視,但其對競爭經濟的倫理基礎也同樣嚴厲批評,而且他對數量方法也甚為排斥。西蒙斯和范納兩人是被一般學者認為與奈特共同是芝加哥學派的創派人物,但這兩人也同樣受到史蒂格勒的質疑。西蒙斯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名叫《自由放任的唯真計劃》(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 Faire),在一九三四年出版,書名雖標榜「自由放任」,卻是一種奇怪的自由放任,因其建議電話和鐵路之類的基本工業應歸國有,他也極力促進所得稅的公平政策,並對廣告之類的商業活動訂定詳細管制,也就是說,西蒙斯的計劃乃是社會主義與私人企業資本主義和平共存,他可能就是當前中國大陸所實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始祖呢!不過,他在貨幣政策上堅決認定必須遵循法則而反對採用權衡性政策來操縱,這也應深深影響往後弗利曼的貨幣思想,而終於形成芝加哥學派的三大特色之一。至於范納這位具十九世紀自由傾向的大師,雖也和奈特一樣對經濟思想深感興趣,而且致力於新古典價格理論的研究,但他卻並不反對數量化的技術,且積極扮演政府顧問的角色,對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也不像奈特那麼地反對,他同時也是將理論應用於國際貿易和貨幣理論相關課題的先驅,范納終於轉向於參與政府事務,其在一九四五年也接受普林斯頓大學的聘約而離開芝加哥。
史蒂格勒之所以不認為芝加哥學派起於一九三0年代,其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充斥著各類人馬,並不純粹抱持相同的信念,不論是在方法論和公共政策上都是如此,其中以「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ist)為代表,這派人物以勞動經濟學家米立斯(H.A. Millis)以及道格拉斯(P.H. Douglas)最有名,而舒茲(Henry Schultz)則是數量方法的權威,是估計需求曲線的先驅,他教授研究所的數理經濟學和數理統計學,而道格拉斯則是衡量生產函數和實質工資與生活成本的領導者。這個領域與奈特南轅北轍,而奈特和道格拉斯兩人之間的恩怨也廣為人知,史蒂格勒在親筆自傳中還特別以專章(第十二章)評述這一場恩怨。
儘管一九三0年代的奈特領軍時期並不被史蒂格勒認為是芝加哥學派的出現期,但至少可說是醞釀時期,因為奈特等枱面人物雖有歧異觀點,但對價格機能和自由市場的看法之崇信和堅守卻是無可置疑的,而奈特對於「團隊」(group或cluster)的培養也頗有成效,被稱為芝加哥學派三劍客的弗利曼、史蒂格勒及瓦列斯(W.A. Wallis)都是奈特的愛徒。
除了學派形成的客觀條件並不十分成熟外,也似乎並無學者在一九三0年代提出芝加哥學派的字眼,甚至於范納和其當時學生也宣稱當時並無明顯的芝加哥學派的名稱或學說之形成,而史蒂格勒也未發現在一九五0年以前的經濟學界有認知芝加哥學派的跡象。直到一九五七年,張柏林(E.H. Chamberlin)在其《朝向更一般化的價值理論》(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Value)一書中專章介紹芝加哥學派,史蒂格勒說這是他所發現最早且最明確介紹芝加哥學派的文獻,而米勒(M.L. Miller)在一九六二年於《政治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一篇文章則是最先完整介紹芝加哥學派及其中心思想的論文。因此,至少到一九六0年代,芝加哥學派就已正式成形而且廣被認同,同時也廣泛受到貶抑。
芝加哥學派之奠基及發揚
芝加哥學派之所以有其不朽名聲,最主要的關鍵人物還是非弗利曼莫屬,他於一九四六年重返芝加哥,此後即致力於奠定芝加哥學派的重要工作,先是將瀕臨暮氣沉沉的貨幣經濟學之研究重現生機,重新賦予貨幣數量學說新生命,不但將之用以研究經濟行為,且對凱因斯學派做了激烈攻擊,甚且得到「反革命」的稱謂。其次,弗利曼極力為自由放任政策辯護,而且提出重要的新政策建議。第三,他以多種重要的方法發展並採用現代價格理論。
弗利曼著重批判凱因斯學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他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實證法則,此即貨幣供給的重大改變與全國貨幣收入的變動息息相關,史蒂格勒推崇弗利曼成功地驅散凱因斯教條,有效地對抗在美國和英國的大多數總體經濟學家之反擊。弗利曼不但承繼了上文所述西蒙斯的固定貨幣供給增加率的傳統,還加以發揚光大,他是個傑出的實證工作者,隨時準備懷疑自己的信念就是某項問題的關鍵,依據實證資料進行最精巧的分析。弗利曼富於辯才,頗有天賦能力來引起對手的憤怒,從而逼使對手花費很多精力來替他的觀點打廣告,迄當時三十多年來,許多有份量的貨幣經濟學研究都出自芝加哥大學,以弗利曼的貢獻最大,史蒂格勒甚至認為,芝加哥經濟學的貨幣面就是弗利曼創造的。
公共政策領域是弗利曼在貨幣之外的另一大伸展空間,不但議題廣泛且見諸多種媒體,《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選擇自由》(Free to Choose)是兩本最成功的通俗作品,而其一大堆演講和辯論,以及擔任《新聞周刊》(Newsweek)數十年的專欄作家,使他在公共政策方面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史蒂格勒特別指出「教育券」(voucher)和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兩個例子,來展現弗利曼在現代價格理論上也有其重要地位,他承繼范納在此方面的傳統,嚴謹地呈現價格理論來指導現代的學生如何使用。
史蒂格勒是芝加哥學派如日中天時的第二大劍客(有關史蒂格勒的生平及學術成就可以參見本書第十章),他在一九五八年重回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擔任第一個Walgreen講座教授2,他是應三劍客之一、當時擔任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院長的瓦列斯之邀回到芝大,對於領取年薪兩萬五千美元高薪一事,史蒂格勒表現得甚為得意,他同時任教於經濟學系和商學院。而瓦列斯和弗利曼、史蒂格勒走不同的路,他往行政及政壇發展。
除了三劍客之外,芝加哥學派極盛時期的人物尚有許多,史蒂格勒首先提到的是達瑞克特(A. Director),這位特殊人物之所以特殊,據張五常的描繪,達瑞克特雖只有一個哲學學士頭銜,但其智力和深度絕不在弗利曼之下,可是他絕少發表文章,也不喜歡教書,只愛閱讀,他是赫赫有名的期刊《法律與經濟學期刊》第一位主編,但他很少約稿、從不催稿、永不趕印,也絕不宣傳,每年只出一期的期刊,今年應出的往往遲到下一年才問世。但一九五八年底所出的第一期,十篇文章篇篇精彩,讀者無不拍案叫絕。3史蒂格勒是在一九四七年蒙貝勒蘭學會(The Mont Pelelin Society)4第一次聚會後與達瑞克特成為密友的。凱塞爾(R. Kessel)是另一個人物,史蒂格勒形容他是個直腸子,有時稍嫌魯莽,天真又夾雜一些頑固,其專長在於健康經濟學,他早期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醫療學會對猶太醫生的敵意,是起因於猶太醫生有殺價的傾向,曾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此君於一九七五年就英年早逝。路易斯(H.G. Lewis)被史蒂格勒稱為經濟學系的支柱,因其不僅解決系裏行政事務的困難及學生課業上的疑難,同時又重新建構現代勞動經濟學的形式。其他被史蒂格勒提到的人物是羅瑞(J. Lorie,他是現代財務經濟學的先驅)、鄧塞茲(H. Demsetz)、特爾色(L. Telser)、佩爾斯曼(S. Peltzman)、波斯納(R. Posner,此君幾乎是獨立開創了法律經濟學領域,也是聯邦高等法院的法官),以及精通經濟發展的哈伯格(A. Harberger)、詹森(D.G. Johnson)、舒爾茲(T.W. Schultz,一九七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另有兩位特別值得一提,一為舒茲(G.P. Shultz),由於其正直、判斷力佳,行政能力又很好,曾被商學院教授說服當院長,他在一九七三年擔任尼克森總統的財政部長時,曾讓美元的匯率浮動,此後即步入政壇。另一位偉大的人物是寇斯(Ronald H. Coase),他是一九六四年到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對於英文極為精通,是個慧黠而文雅的學者,但他崇尚自然隱居,史蒂格勒說他好像連電話都沒有裝,具有對時髦思潮免疫的獨立性,要不是一九九一年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給他,恐怕連經濟學界都會忽視他的存在,不過,「寇斯定理」的聲名遠播,使產權理論又闖出了一片開闊天空,但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該定理的「真義」,寇斯本人則甚為存疑。5
晚近芝加哥學派的發展
最近二十年來(迄一九九0年代中期),芝加哥經濟學的新領袖已經出現,以貝克(Gary S.Becker)和盧卡斯(Robert E. Lucas)兩人最為重要,前者獲得一九九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後者則有「理性預期大師」之稱,一九九五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貝克極富原創力,將經濟學的適用範圍擴大至諸多領域,其博士論文將經濟學分析應用於種族、性別和其他形式的勞動市場歧視者,因而造就貝克成為「人力資本」的領袖人物,其後他又重振犯罪與懲罰的經濟理論,而在家庭經濟理論的開創上更是成就驚人。6
盧卡斯的理性預期理論旨在鑑別政府(和個人)的行動不會令經濟行為人感到驚訝,譬如說當強大的通貨膨脹快發生時,聯邦準備銀行通常會賣公債給商業銀行,因而整個金融圈就學會預期此種行動,所以會在政策尚未形成前,就採取適當的行動以免自己受到影響,該理論對大多數的傳統總體經濟理論,包括凱因斯學派的理論在內,產生了嚴重的破壞力。7
表面看,似乎貝克致力於個體經濟理論領域,盧卡斯則努力於總體經濟理論的工作,其實他們兩人都以個體經濟理論為基礎進行分析,而且不約而同地往經濟增長理論進行突破性研究。
結 語
芝加哥學派由一九三0年代的隱晦不明到一九五0年代的卓然成形並散放光芒,直到一九八0年和一九九0年的新人物接棒。史蒂格勒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新發展(指貝克、盧卡斯等人的研究)是否能代表芝加哥學派核心思想的延續?」史蒂格勒的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是:每項發展都將經濟理論持續,且一致地應用於過去被經濟學家視為「給定」的制度和行為範疇—研究生活中難解的事實,而不是研究理性經濟行為的產物。因此,史蒂格勒接著說:如果在一所大學裏看到類如貝克和盧卡斯兩位經濟學家及其後繼者撰寫否定芝加哥學派傳統的著作時,可就讓人吃驚了。
這樣子的說法也見諸於張五常的著作中,他認為芝加哥學派之所以成為芝加哥學派,說到底,不是因為外間所說的,他們反對政府干預或支持自由市場,而是因為歷久以來,那裏有一些頂尖的思想人物,對真實世界深感興趣,客觀地要多知道一點。張五常又說,在寇斯舌戰群雄的那一夜之前,芝加哥學派早已名聞天下,但當天晚上辯論開始時,反對寇斯者都是贊成政府干預污染的,而反對政府干預污染的寇斯卻勝了一仗,然而,寇斯卻又是贊成政府干預的倫敦經濟學派培養出來的。8
因此,時下有人基於重視市場、崇尚自由經濟已非芝加哥學派的專利,因而認為芝加哥學派應已是明日黃花,但由芝大經濟學系仍有一批智慧人物對真實世界感到興趣,正努力而想客觀地要多知道一點來看,芝加哥學派仍是存在的,也可能永遠持續存在。以此觀點言,一九三0年代時應該也就有芝加哥學派的,只是該名詞的提出可能是在一九四七年於蒙貝勒蘭學會首次會議中而已。—原載於一九九四年十月《美歐月刊》第九卷第十期
註 釋
1. 這裏有必要強調,本文所指,也是一般所認為的芝加哥學派指的是「芝加哥經濟學派」,不是遠流出版公司於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出版的那本書名就叫做《芝加哥學派》(西方文化叢書28號)中所指的芝加哥學派。記得香港《信報財經新聞》「欣然忘食」專欄作者史威德曾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日在該欄寫過,其在倫敦看到此書(原名The Chicago School-A Liber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時以為是評介芝加哥經濟學派之作,即刻購下,回家一讀方知「中計」,原來此書是批評芝加哥社會學派,與經濟學完全無關。
2. 關於Walgreen講座教授職銜有個有趣的來源,一九三六年時,老Walgreen先生為其在芝大的姪女辦休學,並控告學校教自由戀愛和共產主義之類的顛覆理論,該事件被《芝加哥論壇報》炒熱而迫使伊利諾州的議會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芝大後來洗清冤名,Walgreen先生相信芝大無辜,乃贈送五十萬美元給芝大美國中心設立特別講座,二十年後才由史蒂格勒第一位獲得。
3. 這段文字引自張五常〈我所知道的高斯〉,《憑闌集》(香港壹出版公司),頁一0八~一一一。這裏的高斯是香港人士對寇斯的中譯名。
4. 蒙貝勒蘭學會是個很特殊,而在經濟思想上有重要地位的學會,由海耶克發起,第一次開會地點在瑞士的蒙貝勒蘭山舉行而得名,有關該學會的詳情可見吳惠林〈一個崇尚自由經濟的學會〉,《經濟學的天空》,頁一三二~一三七。
5. 可參見寇斯〈闡釋社會成本問題〉,《經濟前瞻》,三四,頁一0七~一二一;有關寇斯的生平和其為寇斯定理而獨戰頂尖二十位經濟學家得勝的記述,可參見《史蒂格勒自傳》第五章,亦可見本書第十九章。
6. 關於貝克的成就請見吳惠林〈擴展經濟學應用領域的奇才—貝克教授〉,《經濟學的天空》,頁一四七~一五三,亦可參見本書第二十二章。
7. 有關盧卡斯的介紹請參見吳惠林〈理性預期旋風來也—盧卡斯教授其人其事〉,《經濟學的天空》,頁一六五~一七一。
8. 參閱張五常〈我所知道的高斯〉,前引文。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
🎯 專題:中共海外升級攻擊法輪功
https://hk.epochtimes.com/category/專題/中共海外升級攻擊法輪功
----------------------
【不忘初衷 延續真相】
📰周末版復印 支持購買👇🏻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