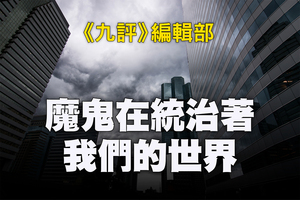機會平等之於現代政治思想,就如同美味之於食物:人人贊成,無人反對。然而,如果每個人都認真對待它,就會導致最極權主義的極權主義,因為要實現機會均等,就必須消除遺傳稟賦和環境影響的所有差異。這就需要從單個胚胎進行克隆培養,並為嬰兒建立電池農場機制。
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人們現在都生活在官僚獨裁統治之下,聯邦機構中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簡稱DEI)部門的解散和禁止,是減少官僚獨裁統治的一個值得歡迎的步驟。當然,有些官僚主義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值得稱讚的,但這不應成為官僚主義機會主義者(bureaucratic opportunists)無休止地擴大其對社會的影響和權力的藉口。
從根本上說,整個DEI活動就是一場別有用心的運動,這究竟意味著甚麼呢?首先,那些長期接受教育的人最終走上了工作崗位,這些人的一生往往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時間是在教育中度過的;然而在教育結束時,他們卻沒有任何明確的技能,甚至沒有任何知識體系,儘管他們擁有豐富的思想見解。正如凱撒(Caesar)在談到卡西烏斯(Cassius)時所說的那樣,這樣的人是危險的:如果不能受僱於那些自詡為受過教育的人設置的職位,他們就會顯得與社會格格不入。
然而,事情遠不止這些。DEI對普通人極不信任。這個運動假定,如果任由普通人自生自滅,他們總會以最惡劣的偏見方式做出惡劣的行為,即使在社會進步的法律障礙已經消除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在美國,至少在兩代人以前他們是這樣的。
DEI運動忽視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那就是,只要生活在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中,即一個不受政府完全控制的社會中,整個群體都可以在沒有政府任何援助的情況下繁榮昌盛。在這樣的社會中,即使是存在社會偏見的群體也能繁榮昌盛,但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繁榮昌盛可能會增加或減少對他們的偏見。人們並不總是為他人的成功而歡欣鼓舞。
在美國以及其它西方國家,印度、中國、日本和猶太血統的外來人口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比其他人口更高的繁榮水平:他們的繁榮不僅體現在經濟上,還體現在文化上。這並不是說對他們從未有過任何偏見,事實上,有時這種偏見非常嚴重;但是,一旦消除了所有官方障礙,他們就做得非常好。甚至可以說,對他們的某種程度的偏見是對他們取得成功的決心的一種鞭策,儘管這決不是這種偏見的藉口。不管怎麼說,他們的成功並不是由任何人宣布的,而是他們自己取得的,因為社會允許他們這樣做。
但是,如果說政客和官僚們害怕和憎惡社會中的一種東西,那就是自發性,因為它威脅到他們的特權。在政治家和官僚中間,控制欲,近乎列寧主義(Leninism)的衝動非常強烈。他們認為,如果沒有他們明智的指導或規劃,社會上就不會發生任何好事:既然他們的意圖是好的,至少表面上是好的,那麼他們的管理就一定會產生好的結果。
有這樣一種假設: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各群體之間結果的所有差異都必須歸因於他們所受到的待遇,而無論如何都與他們的思想或行為方式無關。這種假設是政客和官僚們爭論的焦點。糾正對待人們的方式給後者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工作,因為差異將永遠存在。
此外,有無數種方法可以將人劃分或歸類為不同的群體,比如高矮胖瘦,因此,確保結果平等的工作永遠無法完成。英國小說家 L.P.哈特利(L.P. Hartley,1895—1972年)以其代表性小說《中間人》(The Go-Between,1953年)著稱於世,而在他的小說《表面正義》(Facial Justice,1960年)中認識到並諷刺了以平等的名義消除偏見的企圖。由於人們天生對英俊的人比對醜陋的人更有好感或更熱情,面部正義部門試圖通過強制整容手術,將所有人的面孔歸結到一個平均值,既不會太英俊,也不會太醜陋。這是在1960年,當時沒有人會使用種族公正(racial justice)這個詞,因為擔心會讓人聯想到德國納粹。
當然,如果政府除了消除形式上或法律上的障礙外不採取任何其它措施,而那麼人們受到的偏見待遇就會繼續存在,因為完美並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但是,試圖通過強制手段來培養完全無偏見的思想,不僅註定要失敗,而且很可能總是導致怨恨的道德淪喪,使人們的思想集中在他們不能做的事情上,而不是他們能做的事情上。這樣做的目的據說是為了推動他們的事業,但實際上卻會阻礙他們的發展,儘管這種阻礙並非沒有心理上的回報。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因為所謂的不公正而不能做的事情上,我們至少可以不再認為我們的失敗在某種程度上是自己的錯誤。因此,我們將從個人責任中解脫出來,而個人責任對許多人來說是一種巨大的負擔,而不是一種幸福。並不是每個人都想獲得自由,至少不是每個人都希望獲得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的自由。
DEI運動所承諾的政治香格里拉的問題在於,它永遠無法實現,因為它是遙不可及的。對它的不切實際的無望追尋,會誘發一種有害的宿命論。並非所有的宿命論都是有害的:接受生活是不完美的這一事實會減少因不完美的存在而帶來的痛苦。如果宿命論者接受自己的命運,他的痛苦就會減少甚至消失,然而如果宿命論者怨恨自己的命運,他們的思想就會變成一鍋由不誠實的憤怒和自我毀滅組合而成的大雜燴。
因此,雖然短期內會有一些人會反對取消DEI運動,然而從長遠來看,它將有利於人民的福祉:當然,只要前提是當時間的漩渦帶來報復時,它不會捲土重來。#
作者簡介:西奧多‧達林普爾(Theodore Dalrymple)是一名退休醫生,他是《紐約城市雜誌》(City Journal of New York)的特約編輯,著有《生活在底層》(Life at the Bottom, 2003)等30本書。其中最新的一本著作是《禁運和其它故事》(Embargo and Other Stories, 2020)。
原文:Rolling Back DEI: Resisting Forced Equalit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