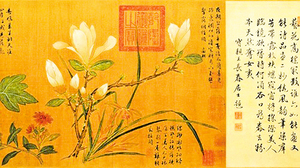汴京城裏樊樓附近,有一家小茶館,很是整齊清潔,所用的茶碗茶具等都是一流的東西,椅子桌子也十分齊整乾淨,所以茶賣得特火。其實,背後的原因不僅如此。
宋神宗趙頊熙寧、元豐年間,有位出身邵武地方李家的書生,在茶館前面遇到一個老朋友,被老友請到茶館裏,互相敘起闊別多年的情懷來。李生有幾十兩黃金,裝在一隻口袋裏繫在自己的胳膊上,隨身帶著,僅防水火盜賊,以免有甚麼閃失。當時正是春天,剛剛由寒轉暖,李生因為熱,脫了件衣服,把口袋裏的金子放在桌上,也沒顧得上及時收拾。不一會兒,有人請他們再到樊樓去聚會喝酒,他就把這檔子事給忘了。到樊樓喝酒喝得特高興,更想不起這事兒了。直到半夜熄燈睡覺了,李生才想到金子丟了!他以為茶館裏人來人往像穿梭一樣,一定沒法兒找了,索性連問也不去問了。
過了幾年,李生又到這家茶館喝茶,喝著喝著就與同伴順便聊起了這檔子事情,說:「我先前曾在這兒丟了一包金子,自己認為這下該狼狽不堪,飢寒交迫,回不了家了,沒想到今天有幸又與您到這裏來了。」
剛好茶館主人聽到他說出這話,就走上前來朝他作了一揖,問道:「先生剛才說甚麼來著?」李生說:「三四年以前,我在貴茶館喝茶時曾丟了一包金子。當時因為被朋友們拉去喝酒了,所以沒有趕來告訴您。」
茶館主人想了一會兒,說:「先生那時是穿一件毛衫,坐在裏面嗎?」李生說:「對。」主人又問他說:「前面跟您一起坐的,是穿一件黑皮袍子的嗎?」李生說:「對。」主人這才說:「這東西是我給收下了。那時也曾跟在您後面,趕著要還給您。可您走得太快,雜在人群裏面認不出來了,我就將它收起來了。心想明兒個您一定會來討。我沒有打開過。只覺得很重,想來該是金子銀子了。只要先生說出塊數斤兩,與口袋裏的東西不相上下,就可以拿去。」李生說:「你果真收下了,我該分一半給您!」主人笑笑,也不說話。
茶館上面用木頭搭了個小閣樓。主人端來一架梯子爬了上去,李生也跟著他上去了。只見上面擺著許多喝茶的人丟的東西,傘啦、鞋啦、衣服啦、器皿啦等等,甚麼都有。每件東西上面都貼個標籤,寫著某年某月某日甚麼樣的人丟下的。是和尚、道士、婦女,就寫和尚、道士、婦女;是各類雜色人士,就寫上推測的話,說某人像商人、像官員、像公差役吏等等;一時沒法兒猜測判斷的,則乾脆寫上不知道是甚麼人。茶館主人在樓角上找到一個小包袱,上面的封記跟幾年前一模一樣,動也沒動;標籤上寫著:某年某月某日某位先生遺失。主人拿了口袋,兩個人又一起下了樓。
到了樓下,主人把喝茶的客人都喊到一起,當著大家的面再一次問李生,包袱裏究竟裝了多少塊金子,一共多重?李生說出是多少塊,多少兩。主人打開一看,與李生說的完全吻合,就拿起包袱交還給了李生。李生分出一半要送給主人,主人說:「先生想來也讀過書,怎麼這麼不了解人啊!區分節義利益,是古人最重視最講究的事情。小人如果重利輕義,就隱藏著不告訴您了,您會怎麼樣?又不能說我犯了法,拿法律來懲罰我。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害怕有愧於自己的良心啊!」
李生知道他不肯接受,覺得十分慚愧,再說不出別的話了。他想重禮感謝主人,請主人到樊樓去喝一頓酒,可主人依然堅決推辭不去。當時在茶館裏的五十多位茶客,都把手放在前額上,無限感慨讚歎,說這是舉世罕見啊!
有見識的人說商朝的伊尹,為官清廉,一塵不染;東漢的楊震,害怕天知、神知、人知、自己知,不做一丁點兒貪贓枉法的事情等等,也不過如此而已。可惜茶館主人的名字,沒有載入國家的史書之中,要是寫進去,也是品質高尚、特立獨行一類人啊!
後來邵武軍管轄下的光澤縣烏州多個李姓人家,為官作宦,頗為繁榮昌盛,就是李生那一宗族的子孫。
(高殿院的兒子高元輔,是李家的親戚,曾跟《摭青雜說》一書的作者王明清詳細談過這件事情。)#
資料來源:宋代《摭青雜說》
看更多 【古道人生】系列
--------------------
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