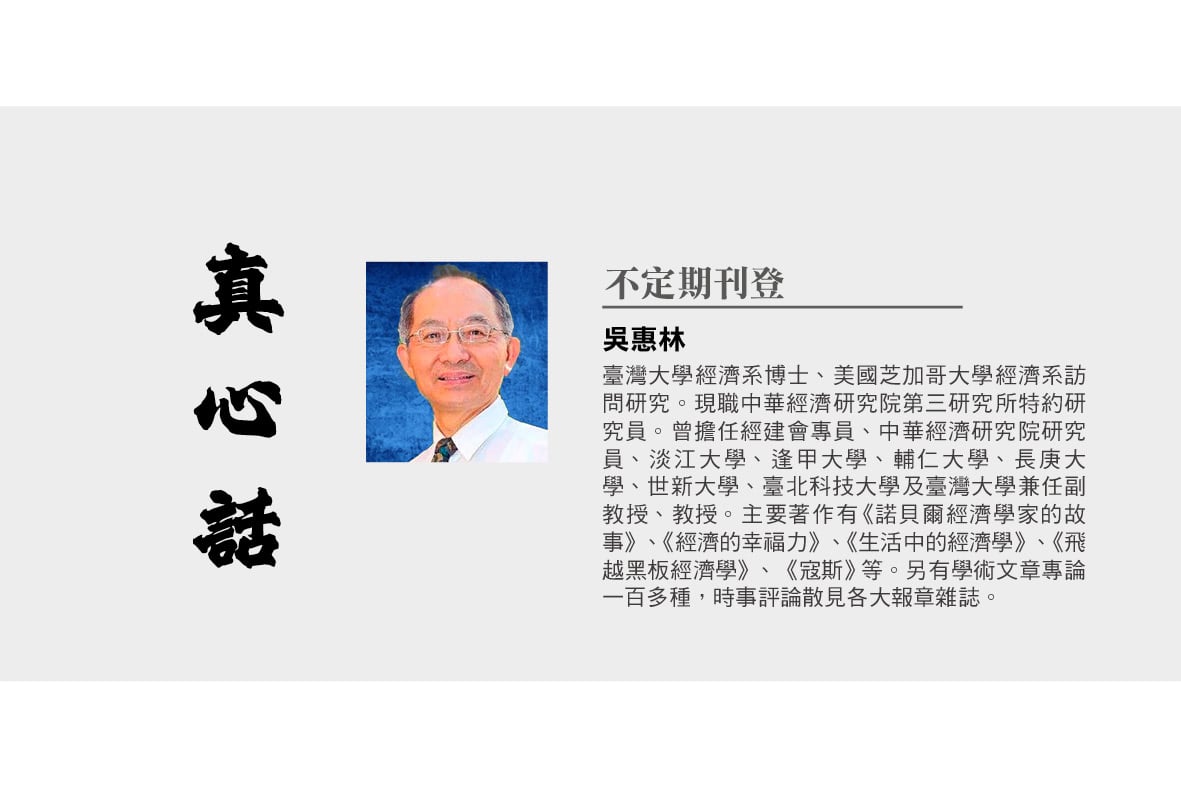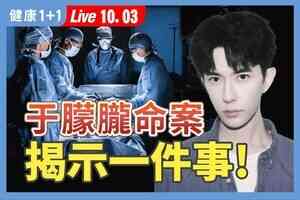「M型社會」早已響徹雲霄,它不只表示貧富懸殊、所得分配不均化愈見明顯,還包括中產階級快速流向下層階級,而「新貧階級」也在社會上逐漸成形。對於這種現象,不只引起各國政府的關切,學者們也都苦心積慮將之作為研究課題。不過,要問的是,這種現象是新生的,還是古早以前就存在的?當今是減輕或更嚴重了呢?有沒有化解的靈丹妙方呢?還有一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最重要課題:人在追求甚麼呢?財富嗎?快樂、幸福嗎?財富或所得能促進快樂幸福嗎?
探索財富所得的增進
經濟學的出現,最被公認的是1776年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那本《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 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國富論》,但這個譯名被有識者認為是不好的,甚至是有誤導性的。)面世之後才有的,而該書講的是「財富(wealth)的成因」,透過「分工」合作最能達成目標。言下之意認為財富的增加得以造福人群。一直到21世紀的今天,這種理念不但沒消減,反而成為各國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標,而「經濟增長率」的追求最能凸顯此情境。不過,在漫長的200多年發展中,卻碰到兩個大問題,一個是「馬爾沙士陷阱」,或者是「人類陷於生存線掙扎」;另一個則是「所得分配」和「貧國如何趕上富國或國際間財富均等」的課題。到了晚近,當環境污染、資源稀缺、氣候暖化等等浮現時,財富買不到快樂或對經濟增長追求的修正,成為新課題。
由於「馬爾沙士陷阱」的存在,經濟學曾被稱為「憂鬱科學」(dismal science),那是因為馬爾沙士(T. Malthus, 1776~1834)在《人口論》中提出「糧食以等差級數增加,但人口卻以等比級數成長」,於是人類難免長期陷於「生存線上掙扎」,當所得增加時出生率升高,人口急速增加,而糧食趕不上,因而每人所得下降又回到悲慘生活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不約而同的追求「經濟增長」,於是「成長理論」和「經濟發展」成為顯學。而跳脫馬爾沙士陷阱的成長模型也出現了,於是「經濟起飛」之後「自力成長」成為可能,在「技術進步」這項因素引進之後,所得不斷成長可以合理解釋。不過,「技術從何而來」和「貧富國家之間成長差距是拉大而非接近」兩大課題卻應運而生。
第一個課題迄今「知識經濟」時代還一直方興未艾,其難免讓人想到「工業革命」時科技的濫觴,而工業革命為何在英國發生、為何會發生又是有趣的謎團。第二個課題到1980年代末期有了新生命,由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 E. Lucas,1937~2023)和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 S. Becker,1930~2014)領銜。前者希望藉由人力資本的加入找出一個模型—一個可以放在電腦裏跑的明顯動態體系—以機械化的運作架構來反映。後者則引進馬爾沙士的經濟動態模型,將人口成長視為內生變數,結合新古典成長模型,重新再出發。之後再有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默(P. Romer)的「內生技術」助陣,將政府在教育訓練和科技政策上擔任「一定程度的積極管理」角色,促進創意、創新的發揮。這些目前還在發展的模型和技巧、策略雖有進展,但一國內貧富懸殊、國際間窮國與富國差距卻仍在拉大,而非洲的赤貧及人民大量死亡也赤裸裸持續著。
除了利用成長模型試圖得到解決之道外,制度改革、直接援助等在著名「休克療法」提出者,經濟發展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2005年出版的巨著《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The End of Poverty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in Our Lifetime)中提到的方式,其實其背後都需有「互助」、「利他」、「愛心」這些基本元素作為前提要件。但在「人心自私、道德沉淪」已經非常嚴重的現時,薩克斯的願望恐怕很難達成。那麼,還有甚麼妙方嗎?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這本2007年出版的《告別施捨:世界經濟簡史》(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又開了另一扇窗。
這本書對薩克斯的「貧窮社會可透過外力介入,達成經濟發展或終結貧窮」的看法提出質疑,作者克拉克是經濟史學者,利用探究世界經濟史的演化推展出「看待全球的經濟發展模式」嶄新觀點。作者以1800年作為分水嶺,之前是馬爾沙士陷阱時代,之後是經濟增長或成長大分流(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時代,正是工業革命出現的分隔。
「文化」是人類窮與富的決定性因素
作者雖然還是在探索「為甚麼地球上的某些地區如此富裕,其它地區卻如此貧困?為甚麼工業革命以及隨之而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會發生在18世紀的英國,而非其它時間或其它地方?為甚麼工業化不會讓全世界富裕起來?反而讓某些地區甚至更加貧困?」這些老問題,但本書提出了引人爭辯的嶄新觀點:決定人類窮與富的命運,並非剝削、地理因素或天然資源—文化才是決定性因素。
一般認為,歐洲在17世紀發展出穩定的政治、法律和經濟機制,從而點燃工業革命的火苗。但克拉克指出這些機制早在工業化之前便已存在,他認為這些機制鼓勵人們放棄狩獵和採集的本能(暴力、沒耐心、不肯努力),接受經濟習慣(努力工作、理性行動和教育),使文化產生緩慢而深刻的轉變。問題在於,似乎只有殖民及保安歷史悠久的社會,才能發展出上述文化特徵與有效率的勞動力,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對於其他許多未能享受長治久安的社會來說,工業化則非天賜之福。
是的,即使在互聯網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時代,世界是平的,人的命運卻不公平,總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工業化榮景無法雨露均霑惠及全球,慈善義舉施捨救濟,無助於改變社會現狀,制度無從致富,「文化」才能決定命運!2024年底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提名的效率部主管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提出「文化」是美國新黃金時代的關鍵因素,他提議「塑造一種文化,再次將成就事業置於碌碌無為之上;將卓越置於平庸之上;將創造力置於循規蹈矩之上;將勤奮置於懶惰之上。」不過,問題是:正確文化如何產生?如何培養?如何生根?或可在這本十七年前出版的書中找找看,並以理性態度予以評斷。
本書除提出嶄新觀點和寶貴的數據圖表外,結論中的一些話語更值得深思,謹摘錄片段與讀者共同咀嚼:
「上帝創造經濟世界的規則,顯然只是要拿經濟學家尋開心。從工業革命開始,經濟模式卻逐漸與任何預測的能力背道而馳,愈離愈遠;各國或各地的所得和財富會在何時出現何種差異,已沒有人能預測。
在現在世界,決定一地民眾工作態度以及合作習慣的社會互動情形,會被經濟制度放大而產生前所未有的極富與赤貧現象。
在我們身處的經濟世界、經濟期刊、研究報告與書籍——致力於資本市場、貿易流量、稅賦歸宿、最高借貸風險、貪腐指數、法治等更詳盡的研究——只讓真相更加渾沌。因為這些著作所建構的世界經濟史,大多缺乏經濟學的傳統要素。
歷史顯示,一如本書反覆提的,西方並沒有任何經濟發展模式可提供給世界其他貧窮如昔的國家。並沒有一帖見效、保證成長的經濟藥方,也沒有複雜的經濟手術可為飽受貧窮所苦的社會緩解症狀。就連經濟援助這種最直接的禮物,也證實無法刺激成長。面對這種情況,若要至少讓一些第三世界的貧民能夠有所獲利,西方唯一能採行的政策便是解除限制,接受這些國家的移民。給第三世界的援助或許會消失在西方顧問或這些社會貪腐統治者的口袋裏。但每多一個移民踏入先進世界的璀璨都市,世上就多一個人的物質生活獲得改善。
還有一個情況頗為諷刺:在世界大部份地區,豐衣足食並未讓我們比我們過狩獵和採集生活的祖先更快樂。幾乎沒有根據支持快樂的增加是來自所得、壽命或健康的改善,舉世皆然。
高所得何以無法帶來更多的快樂?每一個人都可以藉由獲取更多所得、在更好的地點買更大的房子或開更名貴的車來讓自己更快樂,但這種快樂往往是以他人所得較少、住家簡陋與車子破舊的代價換來的。金錢的確可以買到快樂,但這種快樂是從別人身上轉移而來,不是增加在原本共有的快樂之上。
世紀經濟史充斥著違背直覺得效應、意外和猜不透的謎。它與我們是誰、我們的文化如何建立等問題糾纏不清。沒有和這些謎團角力過的人,不配說自己頭腦靈活——我們為甚麼要在荒野度過數十萬年才能達到今天的富足?為甚麼許多社會就是沒辦法和我們在物質的樂土併肩同行?」
每位世人若能反躬自省,並遵循「自助、人助、互助、天助」的文化身體力行,「告別施捨、告別貧窮」或許才有可能,不是嗎?#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