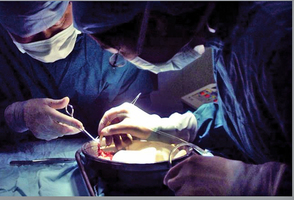《奧本海默》:一部重量級、史詩級的電影(上)
我覺得《奧本海默》這部電影還締造了一項影史上最弔詭的紀錄,那就是:「每一個人都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每一個人看到的內容深度其實大不相同。」電影散場後,尾隨一群觀眾默默離開戲院,我其實很想攔住他們,大聲告訴他們我看到的電影內容,包括那些電影中已經說出來的,還有那些沒有或沒時間說出來的故事。
傳統的物理學中會將物理學家區分成理論型與實驗型兩種類別,理論物理學家通常也是非常厲害的數學高手,擅長用抽像的理論思考與數學方程式去描述複雜的物理世界,而實驗物理學家則是透過雙手萬能、創意巧思、一絲不苟的執著與專注以及永遠懷疑的精神,去驗證、測試甚至發現物理世界。在物理的學術發展史上,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通常理論物理學家也會是一個很糟糕的實驗物理學家,而且越優秀的理論物理學家在做實驗上就會做得越糟糕,經常引起實驗室的小災難。
電影《奧本海默》中的奧本海默就是如此,他年輕時在英國劍橋最著名的Cavendish實驗室做實驗時就非常的挫折,甚至因此產生抑鬱症而發生了毒蘋果事件;他將有致命的有毒物質注射到一個蘋果中,然後放在他的指導教授(一個實驗物理學家)的桌上。這是一個真實的事件,後來是依靠奧本海默家族的關係才得以疏通弭平,但條件之一是奧本海默得接受定期的心理諮商。至於電影中的情節,讓量子力學之父、丹麥籍的尼爾斯‧波耳(Niels Bohr)差一點就吃下毒蘋果,則是純屬虛構。
同樣的,成為華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楊振寧也是一個標準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時也曾經努力去接觸物理實驗,結果當然也是很不成功。楊振寧在他著名的自傳體著作《讀書教學四十年》中就提到,當年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們之間都會相互提醒,有楊振寧的地方就會有爆炸,做實驗時得離他遠一些。楊振寧在實驗失敗的挫折之餘,是泰勒善意地提醒了他,建議他直接用已經完成的理論部份就可以順利完成博士論文了。
畢業以後,楊振寧受到奧本海默的青睞,來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並且開啟與李政道在理論物理上的合作,最終兩人一起拿下諾貝爾物理獎。忘掉是在哪一本書上看到的,據說奧本海默曾經說過一句話,大意是說他在普林斯敦最快樂與滿足的時光,就是能夠看到楊振寧與李政道一起在普林斯頓的草坪上,一邊散步一邊討論理論物理。回想起後來楊振寧與李政道的交惡,再看看電影《奧本海默》與真實世界中,諸多物理學大師們的恩怨情仇,不禁感慨人世間的複雜,即使是最聰明的腦袋、在最純粹的學術領域中,亦復如是。
在西北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後,我從1994年的8月開始在美國紐約州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擔任博士後研究;我的學位雖然是機械工程的力學專業,但我的博士後卻是任職於康奈爾的工程與應用物理系(Engineering and Applied Physics),而它的系館隔壁就是物理系系館。這是一個出過許多諾貝爾得獎主的物理系,因此每次經過物理系館前,都會充滿好奇與敬畏之情。
康奈爾大學坐落在一片綠油油的丘陵地上,冰河時期留下的Finger Lakes與起起伏伏的山巒之間犬牙交錯,因此風景奇佳。大學裏各個建築高高低低地散落在丘陵中不同的位置,而校園裏著名的地標之一,就是物理系館前一片綠油油的大斜坡草地,冬天下雪時上面布滿一層厚厚的白雪,春天來了後則是一片綠意盎然的草皮;因此,快樂的大學生們冬天滑雪板、夏天滑草滑板,在這個斜坡上玩得不亦樂乎。
我的工作地點是在山坡地的上方處,而我中午最喜歡用餐的餐廳則是處於山坡的下方,因此,每天中午我都抱著快樂的心情沿著一條斜斜穿越大草坪的步道由上而下,去享受我快樂的中式美食。吃完中飯後再去餐廳邊的Oline Library,翻閱一下古色古香的中文書籍,心滿意足之後才又慢慢沿著大斜坡爬回系館;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非常愜意與低調的日子。
每天中午沿著山坡往下去餐廳的路上,我經常會遇到一個看起來80多歲的老先生,他看來雖然年紀頗大,但是身子頗為硬朗,經常穿著一件淡灰色的夾克、寬鬆的長褲、一雙略顯老舊的大皮鞋,悠悠哉哉地往餐廳方向前進。他的臉上滿是皺紋,有一個明顯的大鼻子,還有著非常高的額頭,滿頭往後梳攏的白髮在風中胡亂飄著。他的神情總是非常愉悅的,每次當我在行人路上由他的身後超越而過時,都會轉身回頭跟他說一聲「嗨」,而他也總是非常快樂地對我咧嘴而笑,右手在空中揮舞,神情愉悅地回覆我一聲「嗨」。這其實在美國是非常常見的基本禮貌,並沒有甚麼大不了的。
但是,每次我跟他打完招呼,都覺得這位老人的面孔似曾相識,可是一直想不起來在哪裏見過他,直到有一天我因為某件事情進到物理系館裏面,在系館迴廊上看到牆上掛的歷屆諾貝爾獎得主的照片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位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漢斯‧貝特(Hans Bethe),得過諾貝爾物理獎的理論物理學大師。他原本是德國人,在德國出生與完成博士學位,僅僅因為母親那一方有部份的猶太血統,竟然也不能立足於納粹德國,於是在1935年時代離開德國來到美國康奈爾大學物理系,後來因為提出太陽內部的核反應理論與數學計算而獲得諾貝爾獎。
之前我讀戴森的書時,就知道戴森1947年來康奈爾時,就是追隨漢斯‧貝特,做他的博士後研究,而且對他讚不絕口。而費曼也是因為漢斯‧貝特的緣故,才會在二次大戰後,追隨他的腳步來的康奈爾。我在費曼的書裏面經常看到漢斯‧貝特年輕時候的照片,雖然時間可能有差了三四十年,可是我還是可以一眼認出他。
發現這件事情並沒有改變我生活中的routine,每次中午用餐時,如果老遠看到他走在前方,還是會追上去並轉身跟他打一聲招呼;他也是一如往常地咧嘴而笑、揮手打招呼,一頭亂髮在風中飛舞。不知道為甚麼,每次與他打完招呼後我都會覺得心裏非常的踏實,或許是因為覺得這樣的大學中有這樣重量級的大師,是一件讓人非常安心的事情。
我Google了一下,貝特教授是在2005年過世的,享年99歲,距離我離開康奈爾還不到10年。現在回想起來,這其實是一件小事情,不值得大書特書,但是我總覺得這樣的小細節中體現了歐美學術傳統中人性化與人情味的一面,這些所謂的大師們雖然有著超乎常人的心智能力,但是其實都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反觀國內的許多所謂的「大師」們,一旦獲得了某些頭銜之後,往往被一群學生或年輕的學者們左擁右簇,眾星拱月般地被捧上天,有點像日本電視劇《白色巨塔》中,威風的醫院院長出巡時,後面總是跟著一大群穿著白袍的醫生們。每次看到這樣子的場景,我都會想起在康奈爾的斜坡大草皮上,那位在寒風中獨自一人踽踽而行的漢斯‧貝特,以及他那平易近人、親切友善的神情。
電影《奧本海默》中漢斯‧貝特出現的鏡頭也不少,因為在曼哈坦計劃中他是擔任理論組的組長,負責計算所需要使用之放射性元素的關鍵質量,而他日後在美國政府迫害奧本海默的過程中,也曾多次挺身而出,支援他的老朋友奧本海默,是一位備受敬重、人緣非常好的頂尖學者。電影中飾演漢斯貝特的演員在外型上與真實的主人翁還是有一些相似的,唯一的缺點是演員的身材太高了,因此讓我有一些突兀感;看電影時我一直在心中在嘀咕著:真實的漢斯‧貝特沒有這麼高,因為我親眼見過他!#
(2023年電影觀後感)
--------------------
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