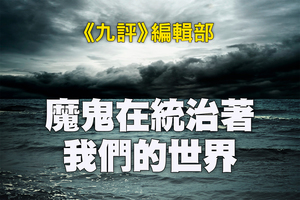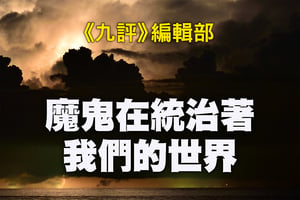(接上文)
2)先鋒藝術背後的共產邪靈
許多世紀以來,古典藝術代代相傳。這種傳統延續到20世紀戛然而止,藝術傳承被一個接一個的激進和前衛的「主義」替代,藝術迅速走向變異,「宏大、鼓舞人心和美麗的(藝術)被新的、不同的和醜陋的代替。」[10]藝術的標準降低,直到降得沒有標準,只剩扭曲的自我表達。人類失去了審美的普世價值。
回顧所有這些新的藝術運動或「主義」的源頭,都與共產主義思潮有著密切關係。其中很多藝術家要麼是共產黨員,要麼是變種共產主義者,或是受這些思潮影響的人。
共產國際的匈牙利文化委員、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acs)創辦了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個任務就是通過背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該文化形式必須排除「自覺地模仿創世主的藝術」。德國社會主義者、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在《審美之維》中稱:「藝術抗議並超越現存的社會關係,它顛覆佔統治地位的意識,也就是日常經驗。」[11]也就是說,他們要鼓動藝術去反神、顛覆傳統道德。此類觀點主導了現代藝術的走向。
法國現實主義畫派的開創人庫爾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參與者之一。他當選為「公社委員」以及激進藝術家組織「藝術家聯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改造」舊制度和建立新的美術趣味的工作。在庫爾貝的授意下,聯盟拆毀了一座新古典主義建築物──旺多姆紀念柱(Vendome Column,後被重建)。庫爾貝否認人類是上帝創造的,著意表現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唯物主義。他的「名言」是:「我不會畫天使,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12]庫爾貝一邊搞革命,一邊「改造」藝術。他的畫以「現實」之名,用醜陋代替美,將畫暴露的女人,特別是畫女性生殖器作為其「革命舉動」,以實現對傳統的反叛與顛覆,配合煽動共產運動。從庫爾貝的人生履歷中,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和現代藝術在誕生之初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在「現代性」思想的影響下,從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開始,藝術家的「革命熱情」持續高漲,一個個藝術運動接連出爐。不同於傳統的流派,這些藝術是一場場斷裂式的「先鋒運動」。「先鋒」(Avant Garde)一詞最早就是被社會主義學者運用於藝術理論,作為與「政治革命」相匹配的文化先鋒。
19世紀末,魔鬼安排印象派登場。從此,現代藝術家們開始了不顧傳統繪畫技法所要求的比例、結構、透視、明暗過渡等等,以追求自我感受為中心的「探索」。新印象派(點彩派)與後印象派相繼出籠,分別以秀拉(Georges-Pierre Seurat)和梵高(Vincent W. van Gogh)為代表,兩人都有社會主義情結。梵高過度酗酒,晚年得了精神病,他的畫作就彷彿是吸食毒品後的人所看到的世界。
藝術作品是創作者和觀眾溝通的媒介,作品中帶有創作者想要表達傳遞的信息。文藝復興巔峰時期的藝術家傳遞給觀眾的信息是善和美;現代派藝術作者放縱自己的主思想,讓鬼和低靈控制自己的大腦,他們本人常常是瘋瘋癲癲的,其作品傳遞的信息是陰暗、負面的。梵高等印象派畫家的許多畫作帶給觀眾的就是朦朧灰暗、陰森頹廢、無理性的感覺。
印象派之後是表現主義和野獸派,再後是由畢加索領頭的立體主義。1944年,畢加索登報宣佈加入法共。他在《我為何成為共產主義者》文中說:「我加入共產黨是我生命和作品中有邏輯的一步,這給了它們意義。」「在被壓迫和反抗中,我不只要用繪畫,還要用生命去戰鬥。」[13]畢加索鼓吹打破傳統畫法,每樣事物在他那裏就像一塊軟泥,任由他捏弄,弄得越怪異,他就越滿意。製造怪異的過程,就是不斷破壞畫面的過程,使之達到一種讓人看後不得其解的狀態。就連和他一起創建立體主義的現代派繪畫者都不喜歡他的作品《亞維農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認為他在「吞油噴火」。[14]
立體派成員之一杜尚(Marcel Duchamp)又發展出「達達主義」,以展出現成物的方式實現對傳統藝術的顛覆和反叛,他因此被稱為「西方現代藝術之父」,導向了「任何東西都可稱為藝術」的理念。德國「達達主義」的行動綱領更是與共產主義直接掛鉤,宣稱:「在激進的共產主義基礎上,一切富於創造的男女實行革命的國際聯合……立即取締私有財產,共同分享一切……要解放全人類。」[15]
達達主義對傳統的狂熱批判,在法國演變為超現實主義,其代表人物是共產黨人布勒東(Andre Breton)。他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式。他反對一切理性、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壓制」,這代表了當時歐洲現代藝術的典型觀點。
其後不斷更迭的藝術運動還包括抽象主義、極簡主義和波普藝術等。抽象主義表達的是情感強度,反映反叛、無秩序、超脫於虛無以及逃避現實的內容。到後現代主義那裏,公認的事實、常規、推理和道德觀念更是被全部粉碎。[16]更有甚者,還有直接褻瀆耶穌和聖瑪利亞的所謂「藝術」作品。[17]
現代派藝術家並非都支持左翼政治,但與共產主義在精神上相投──即以排神、取代神作為人類理性和生存的出發點。這些「主義」一旦得勢,就呈現出滾雪球效應,最終基本上將古典藝術徹底邊緣化了。
3)以醜為美,顛倒傳統審美觀
各種現代藝術的出現及其後來的發展,以醜為美,徹底顛覆了傳統審美觀,甚至達到了怵目驚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杜尚在小便池上簽名,以「泉」為題在紐約展覽,雖然當時被拒絕展出,這種「惡搞」卻被後來的藝術家和藝術院校認為具有「開創性」。至此架上繪畫空前地被否定,裝置藝術隨之興起。伊夫祈因(Yves Klein)於1958年在巴黎依麗絲克雷爾畫廊舉辦一個名叫「空」的展覽,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無物的四壁。
德國先鋒藝術家的精神領袖博伊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個頭部塗上蜂蜜和金箔,懷抱一隻死兔子唸唸有詞三個多小時──《怎樣向一隻死兔子解釋繪畫》。博依斯認為「人人都是藝術家」,有一次,一個人實在忍無可忍地質問博伊斯:「你講了太陽底下所有的東西,就是不講藝術。」博依斯平靜地回答:「我認為太陽底下的所有東西都是藝術。」
現代主義藝術代表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裝在90個小罐子裏當做藝術品出售,名為《藝術家之糞》(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個大便罐頭在倫敦以182,500英鎊售出,相當於差不多20.3萬歐元,是當天同等重量的黃金價格的數百倍。他還直接在脫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簽名,給那些讓他簽字的裸女命名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進行展出。
還有女教授脫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畫家用動物糞便亂塗的東西居然還得了著名大獎。中國有的所謂「藝術家」赤身裸體,全身塗滿蜂蜜和魚油,讓蒼蠅沾滿自己的身體。這種場景讓人感覺到生命是下賤、醜陋和噁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調查中國「極端藝術」的紀錄片「Beijing Swings」中,有一個所謂的行為藝術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Waldemar Januszczak評論道:「中國正在製造全世界最離譜、最黑暗的藝術。」[19]其實,這是人追求魔性的結果。一些所謂「現代藝術」的齷齪噁心、下流無恥其實早已超出了人類的心理承受極限,「先鋒派」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場藝術領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這種潮流讓藝術界搞現代主義的人如魚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畫家們舉步維艱,嚴格遵循傳統、刻苦磨練真正的技藝的畫家和雕塑家甚至沒有了生存的空間。就在1922年,英國拉斐爾前派及新古典主義畫家高多德(John William Godward)由於其嚴謹寫實的古典風格在推崇畢加索亂畫風格的美術界受到歧視而自殺身亡,據說臨死前他留下一句話:「世界沒有大到能同時容下我和一個畢加索。」[20]
魔鬼敗壞音樂的方式也採用類似的手段。正統的音樂符合樂理和規範,音律和隨之產生的各種調性和調式來自於和諧的自然規律。神創的宇宙是和諧的,人能夠欣賞宇宙的和諧,產生美感,因為人也是神創造的。現代派無調性音樂排斥調式、和弦和旋律等音樂的傳統元素,結構缺乏規範,是對神傳的古典音樂的否定。無調性音樂和宇宙的和諧對立,這也是為甚麼一般聽眾會感到其難聽刺耳。現代派「音樂家」則用其「審美理論」解釋說聽眾的耳朵必須經過訓練,習慣這種音樂之後才能欣賞它。
現代派音樂奠基人荀伯克(Arnold Schoenberg)在無調性音樂的基礎上,推出了所謂的「十二音體系」,創造了反傳統的音樂技法。荀伯克的音樂在當時被認為是反德國音樂文化的,是對品味、感情、傳統和所有美學原則的背叛。他的音樂被當時的德國人稱為可卡因:「演奏荀伯克(的音樂)和給人們開可卡因店的效果是一樣的,可卡因是毒藥,荀伯克就是可卡因。」[21]後世的樂評人這樣評價,「荀伯克巨大成就的一種體現,就是他過世後50年,還有能力讓地球上任何音樂廳空空盪盪。」[22]
真正使荀伯克被廣泛接受的是法蘭克福學派重要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音樂理論。阿多諾在其1949年寫的《現代音樂哲學》中,用哲學理論「論證」荀伯克的十二音技法達到了音樂創作發展的「巔峰」。這為後世的現代派音樂創作者和批評家廣泛接受荀伯克的「十二音體系」音樂鋪平了道路。[23]此後荀伯克被很多人仿傚,對先鋒派音樂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先鋒派浪潮亦對音樂界產生了重大衝擊。
在用現代派音樂破壞傳統之後,「先鋒藝術」用搖滾樂代替了古典樂在人們生活中的位置。美國共產黨音樂理論領軍人物Sidney Finkelstein公開要求打破古典樂和通俗樂的界限,這導致了節奏強烈的搖滾樂後來滲透美國,將古典音樂和傳統音樂擠壓得只剩下一點極其狹小的生存空間。[24]
搖滾樂的特點是和聲不和諧,旋律不規整,音樂中充滿了節拍、情感的衝突和矛盾,如同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史記》中說,只有符合道德的「音」才能稱為「樂」,而搖滾樂音樂人的生活和創作中的重要主題卻是性、暴力和毒品。
從搖滾樂之後,美國出現說唱(rap)和嘻哈舞(hip hop)等,風靡一時。說唱充滿粗口,以毒品、暴力、髒話來表現對傳統和社會的叛逆。[25]隨著整個社會道德的下滑,過去這種被視為「亞文化」的藝術形式已經入侵了主流社會,並在主流藝術殿堂受到追捧。
前面我們主要闡述了美術和音樂的現狀。其實,整個藝術界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都出現了受現代派藝術的影響,對傳統的創意、手法、技巧的背離的現象,雕塑、建築、舞蹈、裝飾、設計、攝影、電影等等都是如此。許多從事現代派藝術的人都受到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烈影響。如現代舞的創始人鄧肯(Isadora Duncan),本人是雙性戀和無神論者。她反對芭蕾,認為芭蕾是醜陋和反自然的。她本人和100名學生用《國際歌》作為舞蹈主題,在莫斯科為列寧演出。[26]
這些東西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上立足,形成潮流,甚至變成主流,和共產邪靈通過其在藝術界的代理人對神傳藝術的敗壞有緊密聯繫,而在表現上則有一種自欺欺人卻又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邏輯:即如果有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美學理論作為依據,哪怕是垃圾也能成為藝術。
如果仔細審視這些「先鋒藝術」和「傳統藝術」的差別,人們會發現:「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不僅用藝術讚美神,更通過對「美」的呈現來喚起人心中的「真」和「善」,從而維繫著社會的道德;而各種變異的所謂先鋒「藝術」則在竭力顛覆「文藝復興」的所有成就。它們在引導人們欣賞「醜陋」。這種「醜陋」喚起人的「魔性」,讓陰暗、頹廢、墮落、暴力乃至邪惡等負面思維主導人,將神所創造的壯美的風景、人自身的神性、道德以及社會加以肢解和醜化,甚至直接褻瀆神,從而讓人不僅疏離神,也疏離人自身的內在神性、疏離社會和傳統價值。[27]
4)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毀滅人類
文學是一個特殊的藝術門類。它以語言為載體,傳承著神賜給人的智慧,也記錄著人類寶貴的生活經驗。古希臘兩大經典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生動展現了特洛伊戰爭前後複雜曲折的歷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歷史的恢宏畫卷。史詩所歌頌的勇敢、慷慨、機智、正義、節制等美德,成為古希臘文明和整個西方文明價值觀的重要來源。
鑑於文學對人的巨大影響,邪靈操控其人間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製推廣大量的「文學作品」,給世人灌輸魔鬼的意識形態,詆毀傳統文化,敗壞世人道德,散播對人生的絕望感、荒謬感、虛無感,讓人整體適應魔鬼統治之下的邪惡、變異的污濁世界。文學成為魔鬼統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輸魔鬼意識形態的是共產黨徒宣傳共產主義的各類作品。巴黎公社被鎮壓後,公社委員歐仁鮑狄埃創作了《國際歌》,叫囂「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揚言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國際歌》成為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會歌,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歌,在世界各國共產主義者的集會和文藝作品中廣為使用。
在蘇共和中共歷史上,共產黨為了給民眾洗腦,也指使其文人採用相對傳統的技法,表現「無產階級」的生活和「階級意識」,圖解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出產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蘇聯小說《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都曾經起到巨大的宣傳作用。共產黨把這種風格的作品稱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毛澤東把這種文藝的功能概括為「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服務」。[28]這種文學的意識形態灌輸功能非常明顯,對此人們已經有相當清晰的認識。但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敗壞人類的手段並不侷限於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學破壞傳統。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一個重要步驟是詆毀神傳給人的正統文明。不管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邪靈都利用具有邪惡變異思想的文人,創作和傳播扭曲及辱罵傳統文化的作品。在所謂「新文化運動」當中憑著對傳統的惡毒攻擊而一舉成名的魯迅對中國歷史的態度是全盤否定。在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裏,他借人物之口宣稱:中國的歷史上只寫著兩個字──「吃人」。就是這個魯迅,被毛澤東吹捧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毛還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歐洲,1909年意大利詩人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發表《未來主義宣言》,號召全面反對傳統,頌揚機器、技術、速度、暴力和競爭。俄國詩人、共產主義者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1913年發表《給社會趣味一個耳光》,也表達了和俄國傳統的文學趣味決裂的決心。
第二,以「表現現實」之名,表現醜惡。文人、藝術家用文學和藝術表現醜陋、怪異、恐怖的事物或場面,最常用的一個藉口是「表現現實」。在他們看來,古典藝術強調和諧、優美、清晰、節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導致表現現實時要進行選擇和加工,作品無法做到絕對的真實。這種觀點實出於對藝術的起源和功能的誤解。藝術雖然來源於生活,但卻應該高於生活,才能給人健康的娛樂和高尚的引導。因此,藝術家創造時必須對表現的對象進行選擇、提煉和加工。一味強調「寫實」,實際上等於抹殺了生活和藝術的界限。如果這種絕對的「寫實」就是藝術,那麼每個人的所見所聞就是藝術,又何必花費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培養藝術家呢?
第三,利用文學敗壞道德。邪靈操縱其人間代理人,製造了包括「表現真實的自我」、「自動寫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藉口,其目的是讓世人摒棄正統的道德標準,放縱人性惡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國共產黨人、詩人布勒東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如此界定這個新的文學主張:「純粹心靈的自動主義,意圖運用這種自動主義,以口語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來表達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聽命於這種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賴任何美學或道德偏見……」[30]
「意識流」寫作與超現實主義的「自動寫作」密切相關。由於受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影響,從20世紀初開始,一些西方作家開始進行「意識流」創作實驗。這類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 anti-hero)為中心,情節簡單,通過內心獨白、自由聯想等,呈現個人內心隱秘的思想活動。我們知道,人性當中善惡同在,人在一生當中,要通過不斷的道德修養和自我克制,不斷提高自己,把自己變成一個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現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著不少惡念、慾望;如果以一種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檢束地把自己的各種思想意識呈現在公眾面前,就等於用一個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污染全社會。
第四,以「批判」、「抗議」之名,放縱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裏的文人和藝術家,在反傳統思想的影響下,視一切法律制度、社會規範和道德信條為限制和壓迫。在有些情況下,他們看到了現代社會的某些問題,也看到了人性的弱點。但是他們不是理性地思考和應對,卻以「批判」、「抗議」的名義,走向放縱個性的極端個人主義。為此,他們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懶惰、各種慾望、性的衝動、攻擊性、對名利的追求等等,藉助於變異的手法表達所謂「抗議」。但是,放鬆道德的自我約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只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風雲一時的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為很多具有反叛意識的人所推崇。他的長詩《嚎叫》(Howl)描寫了酗酒、性濫交、注射毒品、雞姦、自殘、嫖妓、裸奔、暴力襲警、偷竊、漫無目的的遊蕩、瘋癲等極端的生活和心理狀態。隨著反文化運動被體制承認(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進入各種文學選本,獲得了「文學經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認自己早年是共產主義者,並表示對此並不後悔。[31]他崇拜卡斯特羅和其他共產獨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戀和戀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學傳播色情。進入20世紀以後,文學作品開始露骨地表現色情內容,某些作品中黃色片段俯拾皆是,卻成為受人吹捧的「經典」作品。很多評論家、學者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吹捧這類作品多麼真實、藝術手法多麼高超。我們知道,傳統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發揮作用的,不管以多麼冠冕堂皇的藉口打破這些禁忌,都是在敗壞人的道德。
第六,讓低靈爛鬼通過文學控制人體。過去幾十年來,隨著人類文化的日益複雜,出現了大量的所謂「類型小說」(genre fiction),包括驚悚、恐怖、靈異、幻想等等,邪靈、撒旦操縱的低靈爛鬼可以通過其中部份作品侵襲、控制人的思想,進而控制人體。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歷史上聞所未聞的變異現象都跟低靈控制人體有關。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學藝術墮落到成為魔鬼的順手工具也經過了相當長的過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寬了文學對生活的表現範圍,一些醜陋、怪異的現象,人的極端、瘋癲的精神狀態,通過文學作品進入大眾的視野。幾個著名的英國「浪漫派」詩人因為其寫作題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稱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詩人。現實主義打著再現現實的旗號,開始表現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份,某些作品過度渲染變異思想和不道德行為。一位文學批評家說現實主義是「四足著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義」。[32]自然主義把人的道德墮落歸因於社會環境和家族遺傳性精神病,這就替個人開脫了道德責任。唯美主義提出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強調藝術的功能在於給人提供感官的愉悅,而不應該承擔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實上,任何藝術作品都對人的道德有著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鼓吹藝術不承擔道德功能,無非是為藝術承擔「不道德」的功能打開閘門。不能否認,這些形形色色的文學流派創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準的作品,但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雖然不能說共產邪靈直接操縱了這些流派,但其中的負面因素顯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後的表現,它們為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敗壞人做了鋪墊。
一個人在寫作時,他的道德水準、精神狀態都會反映到作品中來。隨著人類道德的整體下滑,作家群體的思想當中負面因素也漸漸佔據了主導地位,創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讓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獄。
結語
藝術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藝術可以歸正人心、提升道德、調和陰陽,甚至達到與天地、神明的溝通。
但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共產邪靈通過其在人間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創作出數量極其龐大、種類極其繁多的「藝術」作品,引導人反神、排神、褻瀆神、反傳統、反道德,魔變整個社會,說驚世駭俗已不為過。
對比傳統藝術之美,今天的現代藝術可謂醜陋怪惡到了極點,人類的審美觀念已被徹底顛覆。「先鋒藝術」大行其道,賺得缽盆盈滿。而曾經被視為神聖高雅的藝術,如今被高度娛樂化、庸俗化甚至魔化,變成了可以被大眾隨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對象,甚至是滿足人的慾望和發洩魔性的工具。美與醜、雅與俗、善與惡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顛倒。魔鬼的醜惡、無序與陰暗被構建成「普世價值」,人類社會充斥著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挾著,加速走向墮落和毀滅。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與傳統,人類才能重新走上藝術復興之路,重現真正的藝術的美、神聖與輝煌。#(本章完)
*****
[10] Rober Florczak, “Why Is Modern Art So Bad?” Prager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I07egoefc.
[11] Herbert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ix.
[12] “Gustave Courbet Quotes,” http://www.azquotes.com/author/3333-Gustave_Courbet.
[13] Pablo Picasso, “Why I Become a Communist,” http://houstoncommunistparty.com/pablo-picasso-why-i-became-a-communist.
[14] Robert Hughes, The Shock of the New: The Hundred-Year History of Modern Art—Its Rise, Its Dazzling Achievement, Its Fall (London: Knopf, 1991), 24.
[15] Richard Huelsenbeck and Raoul Hausmann, “What Is Dadaism and What Does It Want in Germany?” in Robert Motherwell, ed., The Dada Painters and Poets: An Anthology, 2nd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89).
[16] Michael Wing, “Of ‘-isms,’ Institutions, and Radicals: A Commentary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Ar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 The Epoch Times, March 16, 2017,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of-isms-institutions-and-radicals_2231016.html.
[17] Katherine Brook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ontroversial Artworks Is Making Catholics Angry Once Again,” Huffington Post, May 13, 2014,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5/13/piss-christ-sale_n_5317545.html.
[18] Arnaud Hu,〈泛談當今的美術〉,正見網,2017年4月30日,https://www.zhengjian.org/node/158434。
[19] “’Baby-eating’ Artist Sparks TV Row,” BBC News, December 30, 2002,http://news.bbc.co.uk/2/hi/entertainment/2614643.stm.
[20] “John William Godward: Biography,” Heritage Auctions.
[21] Walter Frisch, ed., Schoenberg and His Worl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94.
[22] Norman Lebrecht, “Why We Are Still Afraid of Scoenberg,” The Lebrecht Weekly, July 8, 2001, http://www.scena.org/columns/lebrecht/010708-NL-Schoenberg.html.
[23] Golan Gur, “Arnold Schoenberg and the Ideology of Progress in Twentieth-Century Musical Thinking,“ Search: Journal for New Music and Culture 5 (Summer 2009), http://www.searchnewmusic.org/gur.pdf.
[24] David A. Noebel, The Marxist Minstrels: A Handbook on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Music, 44-47.
[25] Jon Caramanica, “The Rowdy World of Rap’s New Underground,”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22/arts/music/soundcloud-rap-lil-pump-smokepurrp-xxxtentacion.html.
[26] “Politics and the Dancing Body,” https://www.loc.gov/exhibits/politics-and-dance/finding-a-political-voice.html.
[27] Michael Minnicino, “New Dark Age: Frankfurt School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Fidelio Magazine, Volume 1, Number 1 (Winter 1992), https://www.schillerinstitute.org/fid_91-96/921_frankfurt.html.
[28]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29]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30] André Breton,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https://www.tcf.ua.edu/Classes/Jbutler/T340/SurManifesto/ManifestoOfSurrealism.htm.
[31] Allen Ginsberg, “America,”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49305/america-56d22b41f119f.
[32] 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19), 104.
--------------------
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