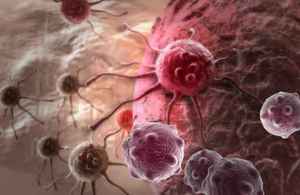「黑狗崽子」之家
1924 年冬月初一,上海霞飛路(現名淮海中路)寶康里31號,一個資產階級的「黑狗崽子」呱呱墜地了。在他之前已有兩個姐姐,兩個哥哥,二哥從小夭折,男的排行他第三,因此叫「老三」。
父親是做棉紗生意的商人,只讀過舊式的師塾。商號取名為「大川通」,主要 是將上海的棉紗運去四川,賣給紡織廠,再將四川的鹽和土特產運來上海。
我家原籍是廣東嘉應州(今梅縣),祖父是有名的中醫,很早就移居四川,而 成了地道的四川重慶人了。
父親由於生意的緣故,長期定居上海,講話的口音是四川上海話:
「好燒,好燒,付要查爛污。」(快點,快點不要耽誤事)
「啥美司,要嘎許多銅鈿?」(甚麼東西,要那麼多錢?)
父親脾氣很好,從不發火訓斥我們,但對我們的教育卻很嚴格,吃飯時,不得 大聲喧譁,吃完飯,碗裏不得有剩飯粒。他經常給我們朗頌詩句: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和哥哥在街上看見大人們手裏拿著 或嘴裏刁著一個白色的小圓卷,點上火, 呼嚕呼嚕冒出很多白煙,從嘴裏進,鼻子裏出,有人還能吐出一圈一圈的小煙環,冉冉升空,甚是有趣。當時不知這就是香煙,以為是一種小玩意兒,哥兩回家後找到一些白紙,將它捲成小卷點燃後,在樓梯夾道中,也呼嚕呼嚕地抽起來,並試著吐圓圈。霎時間,滿樓道煙霧騰騰,我倆也咳得夠嗆。
正在倆人不知所措的節骨眼兒上,父親回來了!一開門,見此情景,二話沒說,立刻打開門窗,並找到了貓在樓道下的我兩。給了我們一人一下重重的屁股巴掌。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溫和的父親發這麼大的火,也是第一次嘗到父親體罰的滋味,有點痛,但不厲害,自己揉揉也就沒事了。
晚飯時,我倆認為肯定要受到父親的訓斥,甚至不准吃飯。沒想到父親一字未 提,好像母親也全然不知下午發生的一場煙災。(父親沒告狀)我兩誠惶誠恐如同嚼蠟似地匆匆吃完晚飯,回到各自的床上,一夜盡做惡夢。
過了幾天,在飯桌上,我們才聽到父親開口說:
「在生意場上,最得罪朋友和同事的事就是,別人恭恭敬敬地遞給你一支煙, 你卻說我不會抽,雖然是婉言謝絕,自己會不好意思,別人也很尷尬。」
父親接著說:「煙這個東西,有百害而無一利,抽上了癮,會很傷身體,咳嗽、吐痰,對肺很不好。高醫生(我家的私人醫生)有好多病人,就是因為長期抽煙,將肺損壞了,咯血不止,得肺癆(肺癌)死的。我寧願得罪人,也不能為了應酬抽上這玩意兒。」
我們心裏明白,父親是在說給我們聽。我和哥哥都低下了頭。正是父親的這一席話和一頓屁股掌,從此,我與香煙就再也沒有緣了。
我們兄弟姐妹的功課平平,尤其是數學,每年都要補考,甚至因此而蹲班留級。父親不得不為我們聘了兩位家庭教師,一位是鄧積仁先生,教語文,另一位是嚴鏡余先生,教數學。
他們都是又有學識又和氣的老師。每次老師來上課,女傭都要為老師們沖一碗 水煮荷包蛋加酒釀。
我們在屋裏亂扔乒乓球,有時乒乓球會落入老師的碗中,老師從容不迫地將球撈出,用手絹擦擦又還給了我們,一句怨言和指責都沒有,還繼續吃他們的荷包蛋。
有次,窗外樓下警察的哨聲大作,兩位老師突然迅速地關上燈,在黑暗中我們 嚇得不敢出聲,哨聲逐漸遠去,我們開燈一看,老師已不知去向。當時我們全然不知老師為何關燈離去,只感到他們好像是羅賓漢式的神秘人物。
直到1949年後,才聽說兩位家教都是中共地下黨員,當時是以家庭教師作為 掩護,實際上是在進行地下活動。那天晚上為了我家不被牽連「窩藏共匪」才關燈離去。
我父親全然不知道他們是中共黨員,只知道他們有學問。父親還資助他們在上 海最繁華的大世界遊樂場附近,開了一家川菜館「錦隆餐廳」。人進人出,生意興隆,這也成了共產黨的一個聯絡點。
鄧積仁的父親鄧夢修,為了躲避軍警的抓捕,逃回四川,途中盤纏拮据,父親 慷慨解囊,為他購買了船票,為此鄧老師和他父親感激涕零。
1949年後,四川進行了大規模的土改運動。我家有田地二百畝,由叔叔經管。 由於鄧積仁已是當時重慶市中共統戰部的部長,他告誡父親要遵守政府的法令積極配合政府進行土改,減租減息。
父親主動交出田契,並帶頭減租減息,還讓我弟弟挑起稻轂上繳政府,表示接受土改的誠意。為此,當地的黑板報還表揚了父親,稱他是開明士紳。
土改結束,我家由一個資產階級的家庭,一落千丈成為一無所有的平民家庭了。父親在土改中積極表現,未受一棍一棒之苦,將土地所有權交給了中共。
由於「朝中有人」,父親拿到統戰部鄧積仁開的介紹信,回到上海在綢布店謀得一個管理布票的職位,工資不高,但生活,醫療和退休都有了保障。
母親的家族都在重慶,外公早已去世,外婆、舅舅以及表兄妹,只在抗戰期間見過面。母親跟隨父親長期住在上海,母親給我的印象是不斷地生孩子,整天躺在床上,吃人參、喝銀耳、燕窩湯。
她前後生了十二個孩子,存活率僅二分之一,四女二男。大姐就讀於復旦大學 商學院,秉承父業;大哥是聖約翰大學的高材生;二姐、兩個妹妹和我都上小學。
母親生育頻繁,體弱多病而缺奶,我們都是由奶媽哺養大的。我的奶媽比其他幾位奶媽的年齡大,因此都叫她大奶媽,她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大包子,是我們的廚師;另一個叫小包子,是打雜,幹零活的。
大姐、大哥可以做新衣服,弟弟妹妹們都是揀哥哥姐姐們的舊衣服穿,頂多是 在過年時套上一件新的罩衫。我奶媽因我老是穿哥哥的舊衣服,經常嘆息:「可憐我老三啊!」
奶媽時不時用自己的錢,偷偷給我買我喜歡吃的零食,因此我從小就覺得奶媽 比媽媽還親。
我們都有奶媽,因此不給我們喝牛奶,這一點我能理解,可是不給孩子們吃水果,我到現在也不明白是為甚麼。以我家優裕的生活條件,給孩子們吃水果,應該說並不是一種奢侈的消費。
每天父親下班回家,晚飯後,丁嫂(伺候父親的女傭)總要為父親削一盤鮮梨,上面還插上牙籤。聽著父親吃梨時,嘴裏叭嗒叭嗒那種享受美味水果的聲音,真令我們這些望梨又止不了渴的孩子們饞涎欲滴,但又不敢上前向父親討梨吃。
我弟弟才四歲,大概實在是經不起父親那叭嗒叭嗒吃梨聲的誘惑,勇敢地趨步 上前,走到父親面前說:
「阿爸,這個梨好吃得很吧!?」父親看著小兒子想嘗梨的可憐巴巴的樣子,用牙籤戳了一塊梨給弟弟。弟弟美滋滋地一邊吃一邊也叭嗒叭嗒地走開了。 我們這些哥哥姐姐們,只能在一旁看著,將口水往肚裏咽了。母親很少和我們交談,她生那麼多的孩子,已自顧不暇,我們又有奶媽照顧,只是在過年時,兒女們穿戴整齊,到母親大人的床前,下跪磕一個頭,給母親拜年,母親賞給每個孩子一塊袁大頭(刻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這就是我們和母親之間一年一度的交流。
只有一件事,令我終身難忘。
我當時就讀於上海市通惠小學,我家住在郊區真茹,我必須住校。每到週末, 我都要去父親的銀行(父親已由棉紗商人轉任川鹽銀行駐上海分行經理)向父親索取乘郊區火車的車費。
學生車票是八角,父親給我一塊銀圓,每週我都有兩角錢的剩餘,這筆錢是我的私房錢,我可以去買彈弓、玻璃球,還有我喜歡吃的拷扁橄欖和排骨年糕。
這天,我拿著父親給我的那塊銀圓,來到火車站售票口,售票員敲了敲銀圓, 的一聲將銀圓扔出了櫃檯:「啞巴!」意思是灌了鉛的假銀圓。我傻眼了,不知如何是好,又不好說這是我開銀行的父親給我的銀圓。我只好收起假銀圓,坐在車站出口處,等我的哥哥。哥哥是初中生,比我晚三個小時下課,我由三點一直等到六點才看見哥哥趕來。他不解地問我為甚麼還在車站,我說售票員說我這銀圓是假的,哥哥拿出他的銀圓對敲了一下,果然我那塊銀圓一點叮噹的回音都沒有,確實是一塊啞巴。好在哥哥身上還有多餘的錢,正好夠我們哥倆 的車票錢。
回到家中,已是掌燈開飯的時候了。母親聽說我因拿了假銀圓,在車站等哥哥 三個小時才一起回來,她一句話也沒提。晚飯後,當父親正在享用他那每晚必吃的鮮梨時,母親發話了:
「雲階,我不明白,你這個做銀行經理的人,難道還分不清銀圓的真假?另 外,給老三的車費就不能多給一塊?要不是老二身上還有多餘的錢,他們恐怕就要在車站上過夜了。」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母親為我的事指責父親,她的聲音很微弱,但字字在理。父 親只得唯唯諾諾,但嘴裏卻嘟嘟囔囔地說:
「這銀圓不是銀行進的錢,是我在外面買東西時找給我的。」
(不分真假)父親在銀行裏掌管全行銀錢往來,但從不摸錢,數錢的事是由我 舅舅和其他職員經手,父親對銀圓,也和我們一樣,真假不分。
自此以後,每逢週末我去銀行向父親要車費,父親還真聽了母親的話,多給了 我一塊銀圓。一塊假銀圓竟換來了兩塊袁大頭,除去車費,每週我的私房錢積存一圓二角,我太富有了,親愛的母親,謝謝您的關心。◇(待續)
--------------------
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