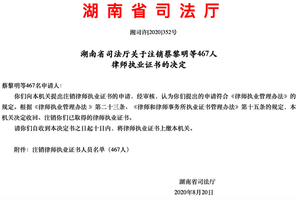按:2017年1月,「709」律師謝陽在監禁中遭受酷刑折磨的證詞震驚海內外,其後,謝陽在中共央視認罪,否認自己遭受酷刑,後被取保釋放。此前,謝陽曾在陳建剛律師發佈的《會見謝陽筆錄》中表示:「如果將來我有任何認罪的表述,都是一種交易。我知道我家人迫切想見到我,我父母都年邁了,非常思念我。」
我只有這一個軟肋
記者:您曾公開表示,您「和當局有交易」?
謝陽:我的案子是在2019年的5月8日開庭,為甚麼選那天呢?因為第二天,5月9號,是我母親80歲生日,所以他們趕在這個點上,如果過了這個點,我可能就不會和他們妥協了。
我母親的生日對我非常重要,那是肯定的。我沒有其它的軟肋。我們家有六個子女,我排老五。母親很疼愛我,我從小就比較聽母親的話。
我最後和當局做了交易,放出了狠話:「如果你們不答應我的條件,5月8號開庭,我就一切推倒重來。」所以他們也小心翼翼地跟我講話,只要他們不答應條件(具體條件我現在還不能說),我就一切都推倒,重來。
我做人的一個原則,就是我可以自己打我自己的嘴巴,但我不能打別人的耳光,我要確保辯護人的安全。
記者:他們怎麼知道您非常孝順,母親的生日對您很重要?
謝陽:當時長沙市國保支隊,是幾十號人馬對付我一個人。我從母親肚子出來以後,上學、參加工作、考律師等等,我接觸的人和事,他們都全方位進行了了解,一個一個進行摸排。他們一直跟我談,終極目的就是想抓住我的軟肋,我只有這一個軟肋。
記者:據《會見謝陽筆錄》,如果您不認罪,他們拿家人威脅您,說要對他們怎麼怎麼樣?
謝陽:是,我夫人和哥哥是國家公職人員,他們威脅說要找他們的經濟問題。
他們還說:「你老婆孩子開車的時候要注意安全,現在這個社會交通事故比較多。」
當時我覺得,我根本控制不了外面的事情。我告訴他們,第一,如果我哥哥、我夫人有違法行為,你們應該追究他們行政或刑事責任,如果明知他們有違法犯罪行為,你們不履行職責,我出來以後可能要控告你們不履職。
第二,兒孫自有兒孫命,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照顧孩子的成長。如果我無法履行做父親的職責,那將來我會把道理和她講清楚。孩子的成長,也許需要比別人更多的代價,那是環境造成的,我無法承擔。
當時他們也找過我父親,讓他到看守所來做我的工作,我父親不同意。當我知道父親這樣的狀態,對我來說確實也是一種鼓舞,我父親以前是水利局的工作人員,他是中共黨員、退休幹部。
記者:您一開始學的專業就是律師嗎?
謝陽:我是中南大學畢業,學工程機械,是個理工生。我們那個時候,孩子一考上大學,跳出這個農民,就是吃國家糧的,不會過多想甚麼事情。我也一樣。
當時考律師,就是因為律師掙得多,工作時間不受約束;而且年齡越大,律師的收入可能會越好;而如果是從事技術領域,你很快就會被淘汰了,技術發展太快了嘛。
因為打賭 我成了維權律師
記者:那您怎麼走上維權律師的道路?這與您當律師的初衷也不一樣啊?
謝陽:開始我就想做商業律師,但拿到律師證不久,我就碰到了一件事情,完完全全顛覆了我之前的思維邏輯。
我和一個朋友聊天,他聊到山東臨沂沂南縣東師河村,有一個叫陳光誠的赤腳律師,說他被拘禁在家裏,裏三層、外三層,沒人能見到他。
我覺得一個刑滿釋放人員,應該是個自由人。政府花那麼多人力物力去維穩他一個人?這超出我的想像,怎麼會有這種事?不可能!
我不相信有這種事,那時我不上微博,根本不知道外邊是甚麼樣嘛。朋友說你不相信,那咱倆就賭吧。他給我設賭注,說如果我到了東師河村,在門口村委會拍一張照片,就給我1萬;我到陳光誠家門口,給我2萬;如果我能與陳光誠本人合照,給我5萬。
當時我覺得這錢好賺啊,那一個人我就上路了。那是2011年11月,我拿到律師證剛剛4個月。當時我40歲,是個戶外運動愛好者,喜歡遠足。
沿途走的時候,有人就反覆跟我講:趕緊回去吧,否則可能會挨打,以前去過的人都挨打!我一聽就樂,更不相信了,我走路,你打我?你總要先警告再打我吧?那我就走唄,我總不至於要挨打去賺這個錢啊。
一路平安無事。我走麥地,東拐西拐,就到了東師河村,離陳光誠家越來越近了。
我有很強烈的好奇心,想看看到底甚麼情況。我準備繼續接近他家的時候,就有四五個人過來了:你幹甚麼的?我說,不幹甚麼,我就是過來玩的。
話還沒有說完,我就被控制了。他們抓住了我,把我的毛線衣翻過來,捆縛了我,臉都蒙上了。我被按在地上,一頓暴打。
打我的人都穿便衣,但他們用對講機,呼喚其他夥伴往這個地方集結。他們打我時,周圍有十多個人,都在旁邊種麥子呢,真的很奇怪,他們甚麼話都不說,沒有一個人出來說句話!
然後我被拖進一個改裝的麵包車。他們命令我跪著,而且腦袋、膝蓋和腳趾這三個點必須要著地。
後來,來了一個自稱是甚麼派出所的警察,我被蒙著頭,看不見,就聽見他說,這個地方經常丟牛、丟羊,他問我說,你是不是偷羊的?我回答,我不是,我是個律師。他說,律師怎麼了?律師就不偷羊嗎?我就無話可說了。
折磨我幾個小時後,他們就把我丟在車上,開車走了。去哪裏?不能問,一問,就是一個拳頭,他們不用嘴說話,他們直接用拳頭跟你對話。我的頭幾乎被他們打裂了。當時特別恐懼絕望,我以為他們要弄死我。
走公路、山路,最後他們開了幾十公里,把我一個人扔棄到一個山洞裏,就跑了。我從洞裏面爬出來時,天已經黑下來,我不知道在哪兒,所有的東西都被他們洗劫了,手機、身份證、律師證包括銀行卡,甚麼都沒有了。
後來我自己下了山,也沒錢,請求人搭車,輾轉才回了家,身上都是傷。
與我打賭的朋友人很好,我挨了打嘛,又被洗劫了,所以最後還是給了我1萬塊錢。
這個國家的改變 需要更多人站出來
記者:探訪陳光誠這事對您影響非常大?
謝陽:對,這個國家居然花這麼大的精力,用老百姓的錢去對付一個盲人!老百姓沒有一點點話語權!
這個社會為甚麼這麼壞那?我從來不看好中共這個體制,我想過它可能很壞,但是沒想到它壞得這麼徹底!這件事完完全全改變了我!
這事以後我開始思考,沒有約束的公權力,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災難,一個沒有公權力約束的組織,就是流氓組織。
因為一個打賭,我以後的路就改變了。這事導致我後面的案源基本就都是維權案件了,我成了一個敢說話的人。所以我還沒有開始做商業律師,就發自內心要做維權律師了。
記者:建三江及慶安事件您都參與了?
謝陽:後來我加入「中國律師團」,這是對社會有高度關注度的一個群體。幾乎每天我都在網上看公共事件,但是並不主動,我就觀察,當我發現沒人去的時候,我就去。
這個國家的改變,需要更多人站出來。一方面讓更多人走出來,一方面我自己要做一個表率。
建三江事件時,我一直沒動,我想大家一起,才能把火燒得更旺一點,我希望更多人參與。
後來建三江幾撥律師都被抓進去了,公民也抓進去了,之後,建三江就沒有抗議的聲音了。那時我認為,艱難的時候,如果不堅守,前面的努力可能就廢掉了。所以我立馬訂機票,一個人就去了建三江。我只是要表明,我們不害怕你們,我們來了。
慶安事件也是第六天我才過去的。謝燕益和李仲偉他們去了兩天,沒有任何消息傳出來。我想,謝燕益第一時間出來說話,可能性命都不保。所以比起這個公共事件本身,我更關心他倆的安全,雖然謝燕益長甚麼樣子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訂機票去了慶安。我比較有經驗,幫他們打了一些條幅,「履行公文職責」、「問責慶安警官」等都是我做的。
記者:「709」一開始您就被抓了,您知道是甚麼原因嗎?
謝陽:開始我也奇怪為甚麼自己被抓。2014年底,我們就內部了解到,當局要整肅一批律師。
在看守所,警察24小時審問我時,我發現他們每天都有一個交接本,每個人來先要畫那個本,我很好奇,裏邊寫的甚麼東西?我想把它拿到手。
後來我用一個辦法拿到了。我發現裏面有五次記錄,他們向北京的國務院辦公廳的一局、公安部的七局、十一局打報告,他們選定了我、廣西的秦永沛及北京的朱孝頂,把我們三人定為「行動派」,從11月份就開始向北京匯報。可能覺得我是個行動者吧。(待續)#
--------------------
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