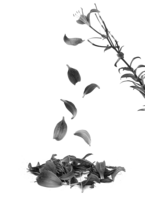1957年中國大地一場政治寒流過後,數十萬知識份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難逃厄運,成了這數十萬「份子」中的一份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攆出上海,押送到皖南山區上海市公安局所屬的白茅嶺農場接受「改造」。
在那裏,我「有幸」認識了陳歌辛先生,原來在那場政治寒流中,陳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終於和我成了「同學」(在改造農場裏,「份子」們是不能稱「先生」的,也不能稱兄道弟,更不能稱同志,彼此只能互稱「同學」)。
陳歌辛先生生於1914年9月19日(皇曆七月三十日),上海浦東南匯人。原名陳昌壽,因希望自己能為人民大眾服務,改名歌辛。是30年代著名音樂家,一生創作歌曲二百餘首,被人們譽為歌仙,中國的杜那耶夫斯基。
1931年,20歲的陳歌辛在玻璃電台邂逅小他3歲的播音員——一位貌美靈巧的富家少女金嬌麗,兩人一見鍾情,很快就墮入愛河,堅定地走到一起。他還為嬌妻譜寫了一首表達兩人心聲的《永遠的微笑》,經金嗓子周璇一唱而傳遍大江南北。
40年代初,陳歌辛創作了中國第一首走向世界的爵士風格、倫巴節奏的《玫瑰玫瑰,我愛你》,他創作的《薔薇處處開》以及《漁家女》等等,我青少年時就會唱。
更因為我也是來自文藝界,和陳先生有更多的共同語言,雖然我們過去互不相識,年齡相差懸殊,他年長我13歲,但在那特殊的環境裏,不期而遇,我們顯得格外親近,終於結為忘年交。
關於陳歌辛先生被劃為「右派」一事,賀綠汀先生生前曾在一次會議上說過:「這頂『右派』帽子本是歸我戴的,後來陳毅保了我,就由陳歌辛『頂替』了。」他就是在這樣一言未鳴、一語未發的情況下,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寫到這裏,不禁使我想起陳歌辛的坎坷遭遇。其實,陳歌辛是一位正直愛國的熱血青年。在上海「孤島」時期,他組織創辦了「實驗音樂社」,積極傳播蘇聯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抗戰勝利後,滿懷勝利激情的陳歌辛,創作了被譽為上海市歌的《恭喜恭喜》歌。
由於他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交往密切,因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出獄後,在上海陳歌辛已無立足之地,他便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去了香港。1949年回到上海後,陳歌辛「左」「右」都不逢源,最終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我們到了農場之後,不久即遇上三年困難時期。勞改農場的物質生活條件原本就難以想像的貧乏和艱苦,更何況我們這些長期生活在大都市裏的文化人,一旦置身在山區的蠻荒環境中,又為了「脫胎換骨」而被迫從事難以承受的體力勞動,在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壓力下,每個人的生命安危都時刻受到無情的挑戰。
到了1961年,勞改農場口糧銳減,每天一乾一稀,「罪人」們在飢餓中艱難地掙扎著。當時農場中流行一種怪病,發病前無明顯症狀,只覺得四肢無力,日漸消瘦,最終導致惡性貧血,臨近死亡時又突然全身浮腫,渾身皮膚腫脹得發亮。
此病發病率高,死亡率也高。陳歌辛先生在農場,水土不服,飲食生活不能適應,幸虧上海親人不斷接濟一些食品和營養品聊以維持生命。但改造無期,天長日久,畢竟生存維艱,求生不易,一旦得病,也就在劫難逃了。
在農場,「罪人」們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通舖,幾十號人乃至上百的「份子」分小組一排排同室同舖並肩就寢。實際上,這裏就是「份子」們的家,吃飯、睡覺、休息、學習(洗腦筋),除了白天上山下地勞動外,所有時間就在自己的床舖周圍轉。
一天早上,大家都按時起床,但陳先生卻睡在那裏毫無動靜,和他鄰床的一位「同學」便走到舖前叫他起床,沒見反應,便用手推他,仍無反應。一時急了,便掀開蓋被,俯首一看,不對了,只見陳先生臉色慘白,停止了呼吸,不知甚麼時候已離開了人世。那一天是1961年1月25日,一代著名音樂家陳歌辛先生,就這樣撒手人寰,無聲無息地走了。
上海市公安局所屬白茅嶺農場,地處皖南丘陵地帶,橫跨郎溪、廣德兩縣,下屬十幾個分場,散落在連綿起伏的荒山野嶺中。白茅嶺農場的改造物件?分兩類:一類是屬於所謂敵我矛盾的勞改份子;一類是屬於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的勞教份子。在那餓殍遍野的年代,在白茅嶺勞改農場,天天有人餓死,被抬到荒山野嶺去草草掩埋。
而這掩埋餓殍的任務就落在勞改犯的身上,而那些勞改犯同樣掙扎在飢寒交迫的死亡線上,自身難保。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餓殍抬到荒山坡上,也只能草草掩埋,這些屍體很快就成了狼群的美食。我是親歷其境的過來人,曾經掙扎在死亡的邊緣。我有時曾想,有些事情也絕處逢生,因禍得福。
我在「反胡風」、「反右」後,兩罪並罰,不僅把我送到白茅嶺農場去改造,而且株連家屬,全家掃地出門,攆出上海,隨我到農場「安家」。這樣一來,或許因為我身邊有親人的同情、照顧和安慰,使我堅強起來,大難不死,撿回一條老命,活到今天。
可憐陳歌辛先生,就只能遺恨終生,餓死在農場了。事後他夫人聞訊趕到農場,尋遍荒山野嶺,只見遍山纍纍白骨,哪來一具完整的屍體?
文革後,我和奇夢石、司徒陽、姚福申等大難不死,先後回到了上海。80年代初的一天,陳歌辛之子陳鋼教授到上海作家協會看望李子雲時,我也在座,交談中他曾向我打聽他父親在農場的情況,我當時只是含糊其辭地應酬了幾句。
因為,一來我經歷了21年的磨難剛脫離苦海,離開勞改農場,心有餘悸,不敢吐露真情;二來我也不忍心把他父親的死因和後事談得太具體,以徒然增加他心靈的創傷。
往事並未如煙。作為親歷者的我,應該拒絕遺忘,搶救記憶,為那個歷史時代留下生命的見證。對我們的後代,應該怎樣去避免曾經發生過的那場人間悲劇的重演,或許有所啟迪。(略有刪節)——轉自《炎黃春秋》2010年第8期◇
--------------------
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